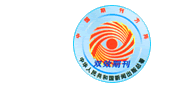大国关系与世界格局新变化 |
||||
|
作者:刘万侠 方 珂 网站编辑:马轩 责任编辑:梁齐勇 来源:前线网--《前线》杂志2018年第10期 日期:2018-10-16
|
||||
|
|
||||
|
[摘要] 当今世界,战略形势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加速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呈现新特征,亚太战略棋局复杂多元。在此背景下,中美俄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大国间竞争与合作并存,但竞争性与对抗性进一步增强。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国际竞争的国内基础,以开放、合作、包容的思路发展国际关系,积极应对,谋篇布局,力争在国际战略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关键词] 国际格局;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8)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西方世界出现分裂、东西方文明冲突加剧、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交织、大国战略博弈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新态势。正确认识大国关系调整以及世界战略格局演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战略筹划必须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 纵观近10年来国际战略形势发展,无论是国际力量格局还是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亚太地缘战略棋局还大国博弈模式,都发生了显著、深刻、历史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国际力量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按照西方的界定,1618—1648年欧洲30年战争及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才开始形成。500年来,国际体系在不断演变发展,但是主导力量始终是欧美等主要西方大国。当前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与历史上相比则有明显不同:首先,就地域来说,世界力量重心正从欧美—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从历史上看,大国的权力转移都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进行的。从最先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后来陆续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形成了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在内的西方强国群体。1913年,这些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占据81.5%的份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53年,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产量占世界的70.7%。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西方七国”(G7,美、加、日、英、法、德、意)从2007年到2017年底,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54.82%下降为46.38%。相比之下,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比较快速的群体性的梯次崛起态势。其中,“金砖五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经济发展虽不同程度地面临困难,但整体实力持续提升。从2007年到2017年底,五国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从13.79%增长为23.09%。 这种巨大的变化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次,就价值体系来说,力量重心从传统的西方民主价值体系向多元价值体系地区转移。通常讲的西方国家,既是经济上的发达国家集合体,又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相似的共同体。但是现在的经济强国,已经不再都是和西方意识形态同质的国家,力量多元的发展趋势和文化价值多元的发展趋势是同步的。再次,原来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成为改变力量格局的重要因素。 全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转变。冷战结束后,西方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全球治理体系形成“美国主导、美欧共治”的局面。随着形势的发展演变,全球治理体系也在悄然发生调整和转变。其原因:一方面,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其国家主权意识、民族意识都在不断强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观念也已形成共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一股力量,在这股力量的制约之下,原先单纯依靠霸权、强制力实现国家目标的方式已经不再像历史上那样有效了。另一方面,新兴大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不断增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比重就发生着微妙变化,新兴大国的投票权不同程度的上升,而西方大国的投票权比重则明显呈下降趋势。长期以来,西方七国集团作为世界最发达的七个经济体,其影响力、话语权是难以替代的。但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这一局面不复存在。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亚太地缘战略棋局发生深刻改变。近代地缘政治学说发源于西方,主要强调地理因素对政治的影响。近代西方的地缘战略理论中,比较有名的包括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和斯派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世界大国一直对欧亚大陆格外重视。长期以来,亚洲的战略棋盘、棋手相对简单。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后主要是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竞争与交流合作。随着亚太重要性的日益增强,在亚太大棋盘上,有更多国家、更多国家组织、更多力量参与进来,使亚太地区形势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从目前情况看,在亚太地区的博弈与竞争中,几个大国包括域外大国和国家组织都希望在该地区掌握主导权、扩大影响力;而亚太地区内的国家,无论国家大小,其纷争的重点则主要集中在岛屿、海域主权、安全及能源资源等方面。近代以来,由于各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增强,国家利益边界的界定极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特别对于领土主权问题,即便是小国,也不会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亚洲各国领土海洋争端矛盾极为突出,域外大国的介入,恰好是利用了这一点。当大国权力斗争、国家间领土主权争端、民族主义高涨、参与主体多元等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亚太地缘战略格局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大国博弈模式呈现新的特征。大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一种综合国力的竞争。20年前,约瑟夫·奈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美国今天之所以能“一超独霸”,经济和军事实力当然是后盾,但是,没有软实力的支撑,美国也不会有今天这种国际地位。当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倡导航行自由、公开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的“大西洋宪章”,明确提出自由贸易、民族自决等理念。这些理念已经深深渗透到今天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理念当中。未来大国的博弈,一国能否在竞争中最终取胜,关键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支撑和制度性创新。经济当然是大国竞争中第一等重要的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支撑国家间持久竞争的关键性因素。文化的因素也很重要,它是一种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增强吸引力和号召力的重要因素。没有文化的力量作为纽带来凝聚民心士气,国家在与外部力量的较量中就缺失了一种精神和信念的力量。制度性创新是关键性因素。16世纪初,西班牙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曾经称霸世界,但很快就衰落了,根源就在于经济发达以后国家完全沦落为消耗型社会。这样一种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导致西班牙缺乏向上进取的机制和动力,所以很快走向衰落。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客观事物一样,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保持发展动力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坚持制度性的创新。 大国互动关系更为复杂、国家间竞争更趋激烈 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既取决于三国自身发展情况,又取决于三国的博弈竞争与交流合作,同时也受国际形势发展演变的互动影响。 从世界格局看,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仍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国际战略格局走向的关键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长期紧张对峙,冷战成为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态势,这一态势一直延续到90年代苏联解体。其间,中苏交恶以及中美建交等中美苏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又深刻影响着国际战略走向。可以看到,中美苏三个大国各自的政策选择以及相互关系的调整变化,成为影响冷战时期国际格局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乌克兰危机余波未平,阿拉伯世界动荡依旧,恐怖主义威胁痼疾难消,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原因与规律,其背后或多或少也具有大国博弈竞争的色彩。由此看来,大国之间关系的冷暖转圜在冷战结束后仍对国际战略形势发展走向发挥着关键作用。从军事实力、地缘影响力、国际话语权乃至综合实力等多个角度评估,中美俄三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的影响力弱化和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推动国际战略格局进入历史性变化的转折期。美国继续维持世界霸主地位,延续其世界领导权和话语权,是其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选择的根本出发点。而中国和俄罗斯则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调整。只要国家目标不同,美国与中俄的战略矛盾就不可能改变,美国对中俄的战略遏制和打压之态也就不可能改变,中俄应对美国战略遏制和打压以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目标的基本态就不会改变。中美俄之间围绕遏制与反遏制之间的博弈角逐就会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存在,并成为推动国际战略格局发展的关键因素。 从力量对比看,美国相对强势、中国和俄罗斯相对弱势的局面仍将保持,但力量对比将逐渐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综合实力是决定中美俄三国国际地位的基础,也是评估三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参考。就美国而言,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科技投入、军费总额都位居世界第一,且近年来经济形势渐趋良好。2017年GDP增长率达2.3%,经济总量达19万亿美元,依然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尽管当前美国发展速度趋缓、实力有所下降,但仍是世界上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就俄罗斯而言,尽管俄罗斯在2008年之前的高油价支撑下经济略有起色,但近几年经济发展缓慢,与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综合国力差距也相应地越拉越大。2017年俄罗斯GDP为1.58万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1.5%,与中美相距甚远。但俄罗斯有自身独有的优势,其庞大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能源储量,仍然能够对世界特别是欧洲发挥独特影响力。就我国而言,经过多年发展,经济总量已经位于全球第二,中国经济增速虽然高于美国,但要赶超美国,仍需时日。中国如内部保持相对稳定,综合实力仍会快速增长。综合而言,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有望保持“一超”地位。中俄在综合实力上相较美国还存在较大差距,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被拉近,中俄与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不断趋于平衡。 从博弈互动看,美俄、中美之间竞争的对抗性上升,但爆发大的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当前中、美、俄“大三角”的可塑性有所下降,敏感性和对抗性有所上升。中美关系对双方而言互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目前中美关系还存在诸多变数和不定因素,但双方关系在曲折中前行,在磨合中渐趋稳定,合作与竞争并存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但如何使中俄双方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多边舞台上鼎力相助,仍需中俄双方加强合作、提质升级。美俄虽多次接触试图提振双边关系,但由于双方都很难做出妥协,致使接触过后依然陷于停滞,双方关系平静中孕育着更大的摩擦危机,美俄关系短期内难有改观。三角关系的“互动感”和“可塑性”下降,中美俄三国关系运行越来越遵循各自规律,中、美、俄关系有逐渐转变为三组双边关系的态势,每一组双边关系都不是绝对的竞争或合作,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另一方面,“大三角”的敏感性有所上升,特别是俄美、中美之间的戒备和对抗性明显增强,但远没有达到引发战争冲突的地步。由于美与中俄在诸多领域依然存在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虽然彼此间防范对抗有所增强,但在利益交织共融的情况下,也有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双方,难以采取战争或正面冲突等极端方式来解决矛盾分歧。再加上中美俄三方在军事力量方面都具备了有效制衡对方的力量特别是核力量,在未来一个时期,美与中俄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保持在较低的区间。 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维护我国国家安全 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世界格局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思想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近现代以来,现实主义权力政治逻辑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大国对于权力的争夺使世界数度陷入残酷的大战状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味强调大国竞争、走大国对抗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在国际关系观念深刻变革、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应以新的思路来筹划和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应坚持以实力为基础的“合作+制衡”的总体思路,其中,合作是发展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制衡是维持国家间力量平衡的重要手段,而实力则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可靠保障。 要把国内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作为运筹大国关系的首要条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大国博弈还是具体的军事竞争领域,综合国力的对比是终极的决定性因素。在综合国力的诸要素中,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尤为重要,它不仅为国家在竞争中夺取主动权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一国国内的稳定提供必要条件。对于大国来说,赢得大国竞争的基础在各自国内,谁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谁能坚持进行制度性创新、谁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活力,谁就能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除非国家核心利益面临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否则都应坚持既定战略,集中主要资源和精力,专注于国内发展和改革,重点解决好国内矛盾问题,夯实大国竞争基础。 坚持以协调与合作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轴和基调。当前,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与此同时,各国也共同面临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恐怖主义蔓延等一系列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在全球性危机面前,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携起手来,加强合作,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推动各国共同繁荣发展。从这一现实出发,结合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及战略传统,中国应始终将协调与合作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在国家利益的框架内加强同美国、俄罗斯在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的合作,在不危及中国关键核心利益问题上,尽量展示积极的姿态,这有利于增强各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 灵活运用制衡手段抑制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虽然大国在处理矛盾问题时都保持一定的战略克制,但由于国内政治需要以及误读误判等各种偶发因素的影响,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在抑制国家间冲突方面,制衡是古老而有效的手段,不以冲突对抗为目的的制衡是维持国家间关系稳定的积极因素。在当前条件下,除利用传统意义上的不同力量(或力量集团)相互间的制衡之外,还应通过增强对地区性问题的塑造能力来牵制对方,同时还可通过对对方盟友施加影响来降低地区事务的敏感度,通过综合性的制衡手段抑制大国动用武力的冲动。 积极塑造对我有利的战略态势,把握主动权。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无论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综合实力方面,还是国际规则制定权、话语制造权等方面,中国与其他大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主动的地位,主动塑造国际态势、主动创造国际环境、主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动争取国际话语权、主动增强国际影响力等,进而影响世界各国国家间关系走向和未来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应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主动参与规则制定、议程设置,投棋布子,谋局布势,以积极心态运筹大国关系、争取战略主动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5](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6](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 [7](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刘万侠,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副主任;方珂,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讲师) 责任编辑 / 梁齐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