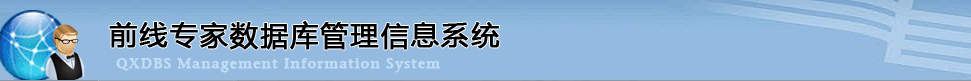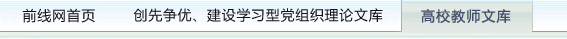|
| 中国立场:和而不同
|
|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030 次
|
伟大的时代大多是转折的时代和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僵化保守思想让位于生气勃勃思想,狭隘的单边主义思想让位于多元主义思想的时代。正是在对东方文化精神之火的“拿来”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近代中国也用西方文化思想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在西方文化借全球化之风而想形成世界性文化一元主导时,中国文化当然应该在检讨西方中心观的同时,废除扭曲的文化交流观,坚持“西学东渐”[1]中的“中学西传”[2]。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输出的内核是:重视原创性的思想创新和高层次的学术输出,保持文化生态而重建中国形象。
“古今之争”强调传统价值的失调。古今之争使我们过去很多问题流传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又不能完全解决,是老问题出现在新语境中。如果把西方之路变成人类最终解答自身困境的根基,危害相当大。应该张扬“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曾经为人类的推进做出过贡献,在今天都应将其好的东西加以整合。未来世界不再是一体化,不再是全盘西化,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现代化其实是有不同争议的。一种认为,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化是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基本上重视物质输出,而第二次现代化强调多元差异,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不再是用物质文明来简单地评价。现代化是人类共同发达的途径,而不是西方发达的途径。人类不是单一模式的未来途径可以规范得了的。“东西问题”承载了过多的人为赋予的因素,而真正的问题—“古今问题”却被忽略了。我们应该超越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体与用,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以“和而不同”的心态看待多元文化。
有人说,当代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很多,应该在全球化中强调一体化、现实性、转向性。我认为在全球化中应把握几个结构性关键:在全球化中的“一体性和差异性”中,应该更注重“差异性”;[3]在后殖民时代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中,应更注重“可能性”;在东方主义的“转向性和立场性”的问题上,应该坚持立场性。不断转向使我们长期透支自身的文化,让外在东西占有了我们,今天更需要表明我们的变中不变的立场[4]。
有人说,文化输出太急了,再等100年后中国成为后现代国家再说,换言之,需等落后的“前现代”的中国追上先进的“后现代”的西方才行。事实上,仅仅用时间的线性发展方式将社会形态分成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不是唯一正确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价值理性,而对工具理性加以警惕。重要的是要有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的态度,要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和的精神。事实上,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来划分社会形态存在很多误区。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 )否定以生产关系划分社会形态,主张按工业化的程度把世界分为3种社会:前工业社会(亚非拉各国)、工业社会(西欧、日本)的新型社会、后工业社会(美国)。这种分法遭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的批评,可惜国内还有不少人抱着这种错误的社会形态划分法不放。我坚持到有两种价值形成的“十字轴”判断,一是横轴所包含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称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时间之轴”。在这一轴的矢量上,传统比不上现代,现代比不上后现代,后现代当然比不上后后什么现代。但人类精神的超迈性还使其有另一纵轴——“境界之轴”:底层是实用境界,中层是艺术境界,高层是思想人格境界。人类在时间之轴上(工具理性)耽误太久,而在空间之轴上(价值理性)又遗忘太久。文化的境界不以是否先进、是否时髦而做出评价的,“文化输出”需要理性地估定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线性进步主义的支配。[5]
有人说,等经济强盛了以后再谈文化输出,中国经济的全面振兴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前奏。如果中国的经济衰微,什么样的文化输出都只会是纸上谈兵,仅仅变成知识份子曾经精神挣扎过的记录而已。但是,如果经济发达了,而人们又成为仅仅看到眼前利益而追逐西方流行文化的群体,那么这事实上是人在无穷欲望扩张中,使“自我”虚无化和生存意义虚无化。自我的虚无使得人成为“非我”,对个体而言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而走向自杀,对民族而言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休克,这在本质上是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但如果中国经济全面崛起,而我们的文化却还没有丝毫准备,那是我们的另一种悲哀。我认为任何对于前途的展望都是一次搏击,都具有一种新的“可能性”。[6]
有人说,中国文化输出是官方的事情,个体作用微乎其微。中国文化输出确乎有一个瓶颈,即“官方和民间”的问题——文化输出究竟是官方的做法,还是民间的做法?应该说,文化输出与国力增强紧密相关,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民间的做法。作为个体,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做文化可持续性发展工作,意义重大。只有个体觉醒了,群体的觉醒才有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既然有了国际汉学,就不需要中国学者的文化输出了。我强调当代中国学者面临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新书写的工作,以及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任务。本土学者可以比汉学家更到位地理解真实的中国形象,结合中西学者阐释中国的长处,整体性地推介中国文化。其目的是让世界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7]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有人说,中国过去一直在“输出”,现在应该不断“拿来”。器物层面的输出是文化输出的最早形式,但更为高迈的文化输出应是思想和艺术层面。以电影为例,张艺谋电影《英雄》送到美国后,批评界出现了很大的文化困惑。过去看张艺谋电影如《秋菊打官司》,一个说陕西土话、又丑又脏、奔走于黄土高原之上的妇女,可以使西方人以文化优越的眼光居高临下地“看”,感受“中国形象”的落后。其他如《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红高梁》,杜撰的民俗风情都让西人看得很开心。在男性中心主义的西方眼中,中国被女性化了,西人已经习惯以西方男权眼光抚摸女性化了的中国形象。但在《英雄》中展示的却是大秦军队的威武雄壮、万箭齐发、气吞山河的气势,那只西方权力之手不再能抚摸了,因为这是自远古走来的一个个轩昂勇武的男人方阵。“中国形象”改变了!电影《刮痧》所展示的显然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差异冲突的问题。“刮痧”后孩子的背好像被打过一样。表面上看,刮痧是通过一个铜板在人体背后的反复摩擦达到治疗效果。使西方人迷惑的是,正是这个铜板在人背后运动后才变紫的,那与“打”有什么区别?刮痧是要顺经络而行,而经络的基础是阴阳的思想,阴阳思想则是中国哲学中的精微部分。缺少了这一文化背景,外国人只能认为,那是一个铜板在背后运动对人体造成的伤害。这已然说明文化隔膜必然导致文化冲突,消除文化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文化输出。有必要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毕竟只是在近200年才落后的,“学西”是应该的,彻底“西化”是不可能的,“化西”更是天方夜谭。应该回到问题的地基上来——学西或西化之后还怎么做?我认为应该是平等对话,既不应是现代化初期的“东化”,也不应是现代化后期的“西化”,而应该是东化西化并行,我称之为多元互动。
有人说,文化输出,西方人不感兴趣怎么办?景教的先例表明,接受对象的兴趣虽是重要的指数,但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前提。[8]中国文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既不能说又不能听的中国,一个只是发展技术和经济的中国不是真正的大国形象。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流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9]这依赖于中国经济起飞、科技崛起和国人自信心的增长。文化输出意味着中国文化应该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源源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文化吐纳”。不管他者接受心态怎样,我们都要放弃对立心态,说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对西方文化拿来中,开始对其质疑、提问、反省、对话,使西方意识到当代中国开始耳聪目明,并且对中国文化不再是俯视而是平视。达到这种文化状态才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成功平台和全球文化正态分布,发现东方的立场才是文化生态的和世界主义的。
有人说,“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容易被西方看成与“自我扩张”的意识相关联。正如我屡次表明的,文化输出不是要制造出一个抵抗性的内在中心以抚平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自豪感所遭受的创伤,从而间接地助长自我优先性和对“他者”的歧视;也不是要在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中确立内部-外部视点,在“普遍性-特殊性”的共谋怪圈中强调以特殊性为认识论基础,从而兜售一种控制他者的权力意志。“发现”首先是重新阐释的过程,一个民族、一个人的重大时期都需要反思精神使我们得以回到本体论根基上。“发现”其实是指中国知识界应该有一种精神的重新觉醒。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觉醒,就会忘记一个事实: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陈序经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文化,而是可以认真思考重新“发现中国”意义的时代。我们永远需要在“发现”中认识我们的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如果不开始思考自己真正的“中国形象”,所谓“拿来”和“发现”就失去了本真的意义。
有人问,文化输出会不会被看成是民族主义的?在我看来,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具有世界主义的文化互动立场,民族主义有的只是偏激的排外主义立场,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主义立场使我更为尊重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每当我在国外看到母语汉字或书法艺术,都会产生一种深沉而持久的激动,难以平抑。这是古老华夏文明给我的精神空气和知识水源,丧失了这一切,作为个体就是无根之人,作为民族就只有短暂的呼吸而走向精神枯萎。我意识到,中国不可能被“他者”正当而平等地发现,我们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自己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发现东方古国经过现代化洗礼以后的新形态。说到底,我坚持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平等对话,任何中国威胁论或者东方威胁论,都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文化转型与文化发展中,只能是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审美共识(不管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才有可能组成为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只有这样的差异性和多元化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维持整个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有人将亚洲称为“筷子文化圈”,我认为应该是“汉字文化圈”。吃饭的筷子可以变成刀叉,它只是一个运作的问题,它不会进入神经、进入身体,化成我们的血肉。汉字则可以进入思维、血脉和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废除汉字。历史证明,离开了汉字,中国文化仅仅两代人就中断了;韩国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假名,在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许多歧义,因为它的名字用汉字表达时是浓缩了的意象。世界各国的本国文化输出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西方国家自不待言,就连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也在积极争夺东亚文化圈的领先权,日本文化的大力输出已经使日本挡在了中国前面,成为西方人眼中东方文化的代表。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江晓原等:《天文西学东渐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3] 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 许宝强、罗永生选编:《解殖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 参皮特•布鲁克史密斯:《未来的灾难: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
[6] 王岳川:《全球化与中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7] 费正清:《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菲茨杰拉尔德:《为什么去中国》,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8] 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3。
[9] 参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