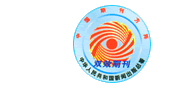中国古代传统政德文化强调为官者必须“戒巫”,即反对封建迷信思想,“为政不尚巫”。吕坤的《治道》就提出:“禁邪教之倡。”严禁官巫合流,严惩巫书,严惩巫者干预政治的言行。汪天赐在《师巫》中就指出:“为政当戒师巫风。”赵素的《为政九要》指出:“当官诫巫,风化自兴。”张居正也认为,执政者绝不能迷信,在《帝鉴》中提出:“妖不胜德,君子之政也。”唐太宗更是指出:“灾祥不胜德,修德可以销变。”张养浩在《牧民忠告》中提出。“当官诫巫,以义取命。”为官处理政事,应以直道为先,应以戒巫之心为先,要识得巫之手法的欺骗本质和社会危害性。南宋大儒吕本中在《官箴》中更是直言:“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当官者为政,坚决不信巫、不尚巫、不师巫,坚决不与巫接触。
戒巫的实质
古代政德中所提出的戒巫思想,实际上就是指反对迷信思想。古代政德文化一直强调官员所肩负的反对迷信思想的任务,显然,这与迷信思想盛行有很大关系。一方面,中国古代有深厚的迷信思想文化根基,比如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文化、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官方所流行的占卜文化,这在甲骨文上都有记载,到汉魏时期有“街巷有巫,闾里有祝”的情形;另一方面,迷信思想流行与生产力低下有很大关系,无论是井田时代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很难依靠人自身的力量改变或预知自然灾害。
古代政德文化之所以强调戒巫思想,还与迷信思想所带来的危害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巫蛊之祸”,即西汉武帝时期和南朝刘宋时期。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巫蛊所带来的危害,才有了众所周知的历史上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除此以外,还有众多官员在坚守传统政德中表现出了反对迷信的坚定性。
治巫的名臣
第五伦(生卒年不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根据《后汉书循吏·第五伦列传》记载,第五伦曾跟随淮阳王到京师,与其他官员一同被光武帝刘秀接见,向他询问治政之事,第五伦趁机回答为政的见解。光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并委任他担任会稽太守。第五伦到达会稽地区之后,首先治理该地大行其道的迷信之风。该地滥设寺庙频繁祭祀,喜欢占卜,百姓常常用牛来祭祀鬼神,因此财产匮乏。第五伦上任后,向所属各县发出文书,明白告知百姓,那些借托鬼神来敲诈恐吓愚弄百姓的巫祝,都要审查问罪。如果有胡乱杀牛的人,官吏就给予处罚。民众开始很害怕,有的巫祝加以诅咒胡言乱语,第五伦却追查得更紧,后来这类事便逐渐绝灭了,百姓因此安定下来。
梁武帝萧衍时,郭祖深为幕僚,曾经一再上书国家治理意见,如清除贪官,要“罢白徒养女”,以禁止寺院势力的强大等,根据《南史循吏·郭祖深列传》记载郭祖深曾这样上书:君子和小人,所想的不一样。君子志于行道,小人盘算得利。志于道者安国济民,志于利者损人利己。僧人是害国的小人,忠良是卫国的君子。臣见患病的人去找道士治病便让你打醮画符,找僧尼则让你戒斋听讲经,民间巫师则要驱妖捉鬼,医生则用药外敷内服,这全在于你自己的事先选择。臣认为治国之本,和治病相似,治病应摒弃巫师鬼怪,去找华佗、扁鹊;治国应当黜退奸佞之徒,而用管仲、晏婴。如今所信用的人,只不过是腹背上的毛罢了。虽然他的意见未被完全采纳,但梁武帝认为他很正直,擢升为豫章钟陵(今江西省南昌市)令、员外散骑常侍。
田仁会 (公元601—679)年,出生于雍州长安,在隋朝时担任幽州刺史,被封为信都郡公。《新唐书循吏田仁会列传》曾这样记载:“巫传鬼道惑众,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会劾徙于边。”也就是说,田仁会在担任幽州刺史的时候,有很多巫士传播死神才会使用的高级咒术,自称能够复活死人,并在市里设置了一尊神。田仁会不信这些妖言惑众的迷信思想,坚决反对,就命令人将设置的尊神搬走。
吴履,字德基,兰溪人,是明朝有名的循吏。少年从师于名士梦吉,熟读《春秋》诸部史书。先担任南康县县丞,后任安化知县,又做潍州知州等,但他不管到哪里任职,他都坚守官员政德,受到百姓爱戴。在《明史·循吏列传》中就记载了他任职南康县时是如何反对迷信思想的,“邑有淫祠,每祀辄有蛇出户,民指为神。履缚巫责之,沉神像于江,淫祠遂绝”。意思是,县里有不合礼制的庙堂,每次祭祀就有一条蛇溜出门,百姓都指着蛇说,神出来了。吴履将巫师捆绑起来责罚,把神像沉到江里,于是胡乱祭祀鬼神的现象就绝迹了。由此,吴履当县丞六年,百姓都很拥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