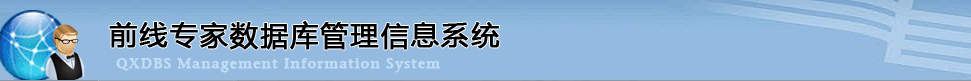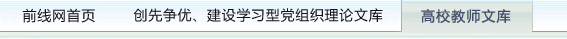| “镜城”风景:中国电影中的北京映像 |
| 作者:陈少远 日期:2013-09-27 阅读:860 次 |
|
梁振华 陈少远 不论是作为技术的发明还是文化的形式,电影都是城市的产物。从卢米埃尔兄弟在咖啡馆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开始,电影和城市就一直保持着互生关系。城市丰富的生活景观和文化景观合乎电影作为视听艺术和时空艺术的本质要求,成为电影的重要题材内容。电影在发展进程中留下大量的城市影像,记录着城市的变迁和发展;电影雕刻着城市时光,同时在光影中对城市进行想象,塑造着城的影像记忆。 伍迪•艾伦镜头下的纽约充满知识分子视角的城市狂想,文德斯站在苍穹下看到了一个诗意又沉重的柏林,杨德昌的城市森林围困着大时代里迷路的台北人;电影在光影声色的流转里捕捉一个城市的神韵和气质,通过空间和文化构形帮助人们感知和再认识城市,塑造着都市的文化结构和城市人的情感结构。城市又是电影生存的土壤,都市文化的底色决定着电影视域的颜彩。电影和城市互为镜像,电影犹如镜子,映照着想象之城;被影像赋予幢幢幻影的城市也成了镜城,上演着一出出虚实交映的城中故事。 作为文化古都和现代都会,北京的城市影像历史并不久远,远不及在上世纪二三年代影像中特色鲜明的上海城,中国电影对北京的想象和文化表达也如雾中风景,呈现丰富性和多义性。 北京和电影渊源久远,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即诞生于北京。但是此后很长时期内,北京作为城市在电影中的表达都是缺失和模糊的,远逊色于文学作品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和记忆。1949年4月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北京在电影史上占据了新坐标;十七年里,新中国的电影创作主要集中在北京。这个时期虽然产出了《我这一辈子》(1950)、《龙须沟》(1952)等城市主题电影,但是城市大多置于叙事之后,语义模糊。这个时期里的北京映像,多是一个和没有现代指向的乡土意象,并且呈现浓厚的政治色彩。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城市形象开始在电影中苏醒,以北京为对象的城市影像纷呈多样,不仅有《城南旧事》、《茶馆》、《骆驼祥子》、《春桃》等回望旧北京城市景观的影片;也涌现了一批表现现代都市图景,与当代北京人状态紧密相连的电影,如《夕照街》、《珍珍的发屋》、《北京,你早!》、《本命年》、《顽主》、《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我的九月》等;以及延续京味特色,表现北京城市井之乐的故事,如《夕照街》、《珍珍的发屋》、《瞧这一家子》。北京以久远的历史沉淀、深厚的文化传统、延续的京味文化、现代都会的开放性为城市电影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文化想象。 新世纪以来,北京在电影文化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京城映像也随着城市的变化呈现丰富的形态和多重的言说空间。北京如一个镜城,绮丽诡谲的光影镜像相互交织、映照,渗透进这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文化性格里。 一 城:影像对北京的空间构形 美国一位学者这样描述北京“北京首先是一个观念,然后才是一个城市……它从中心到边缘创造了一个世界。它虽不用言辞说话,却用建筑、体积、空间来说话。大大小小的厅堂、宫殿、花园、街道、城墙、大门、牌坊、庙宇,一起发出非常清晰的宣言”,城市空间是人们对城市认知、想象和记忆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时空艺术,电影想象和表达城市最直接的载体就是城市空间画面。城市空间对城市的“构形”,是电影最直接的城市想象。 故宫、天安门等标志性建筑出现在许多北京影像中,这是北京作为文化古都、政治中心特有的城市影像符号。但是究城之实质,一个城市的内在气质和文化品格更浸润在城市的社区空间中,北京的空间构形依赖于胡同、四合院、杂院等特有意象。 《我这一辈子》在影片开头呈现北京城市全景,并剪接了一组名胜古迹影像,组成一幅旧北京的城市景观图。由老舍作品改编的电影《龙须沟》是第一批描绘新中国城市的电影作品,故事发生在市井底层的社区单位小杂院里。影片通过天桥、旧街等物象将旧城市景观具象化,创造了一个建诸城市日常生活之上的景观,在新中国成型之初对北京空间进行了重新想象。影片最后通过宽阔的露天表演所完成了新城市景观的开拓,以此打开了北京作为新城市的文化想象的起点。 “胡同—四合院”的社区空间是北京影像中最常出现的空间形象,如《城南旧事》里古都南城的城垛颓垣、闹市僻巷、胡同旧街,《春桃》里三十年代京城的狭长小巷。四合院是一个小型的社团,这个日常空间里的平民生活是北京人城市经验的核心,一个城市精神底蕴的根须深触到锅碗瓢盆、邻里短长里。《城南旧事》里的四合院闲静安谧,花虫草木,自然之乐,表现了这种社区空间“和合”的生活境界和人伦之情。这种社区生活具有稳定的文化形态,寄寓着乡土感情,其所结成的地缘、人缘也是北京在都市化进程中特有的城市文化特色。 杂院居住者多为市井平民,可以视为四合院的变体。《瞧这一家子》、《我的九月》、《找乐》、《剃头匠》、《我们俩》、《卡拉是条狗》等影像纷纷表现了这个城市底层生活空间里的民生百态,形成鲜活的市井景观和城市影像记忆。 城市空间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流动汇集的场所。北京的形象性正是由这些物理空间来拼贴组构,完成空间想象和文化阐释。天桥、旧街、胡同、四合院、大杂院,都是属于北京的成长记忆,也构成北京城乡土特色的文化表达。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自身又不断催生大量新的构形。《北京,你早!》的故事载体是新式交通工具公交车,《开往春天的地铁》里城市人的相遇、离合都发生在地铁里,《顽主》的城市背景充溢着许多陌生、新潮的城市景观。与此同时,这个城市的旧景观却在消逝,宁瀛的“北京三部曲”的创作动机就是记录逐渐消失的胡同、四合院这些古老建筑和大片老式社区。对于老北京城市景观的想象,《我的九月》发生在它的童年时光,《北京,你早!》讲述了它的青春故事,《找乐》里它已经步入老年、步履蹒跚,《夏日暖洋洋》则目睹了它的消散和失落。随着四合院等社区单位逐渐消失,城市本身也在碎片化,加速的空间隔离过程降低了城市人共同生活的能力,记忆中的乡土也变得陌生。《百花深处》寻找胡同最后落空,也暗含了对城市景观消逝的感伤和追忆。 随后,新城市景观渐起,“鸟巢”(中国国家体育场) 、“蛋壳”(国家大剧院)和“大裤衩”(新央视大楼)等“新住户”也频频出现在城市影像中。新地标催生了新的空间意识和空间现象,城市想象进入了全球化想象的幻境,这个城市成了“一个现代巨型都市、一处无名的非地、一个陌生与疏离的所在”。 在城市电影中,城市既是背景,又是无声的叙事参与者。北京的特殊性在于现代城市风景与古都北京的旧迹风情交融共生,从而为电影想象提供了开放的空间和多重言说的可能。新旧城市景观的交叠使得过去、现在、未来共存于北京的城市空间内,北京想象也呈现了多层次和多元化,以及不同思想、价值、文化交融的丰富性。 二 人:影像中的北京人与市井生活 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描述北京城市气质的难以定义“北京拒绝抽象,它似乎只能活在个人的生动感觉中”,北京的文化灵魂内在于居住于城中、浸淫其精神的人。同样地,电影要完成对城市的想象,不仅要通过空间构形,也须经由城中人“流传并内化的文化构形”。 北京的城市文化“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衣食住行中,在最不经意的‘洒扫应对’、‘日常起居’之间”,城市电影通过对北京市井生活、民生百态的呈现,提供了想象和言说北京的丰富材料。生活在胡同、四合院、大杂院里的凡俗人家;深巷市声、坊巷俚语、衣食住行、市井风味;城市影像将镜头对准京味风物、人文景观,在世俗景象的光影里创造了北京的文化序列,这些文化序列蕴含着平实而深刻的城市生活文化内容,也沉淀着北京人的文化意识和伦理观念。 《我这一辈子》是新中国电影中最早碰触城市底层的影片,导演石挥注重表演、台词的生活化,影片在悲凉叙事外注重营造朴实鲜活的生活气息,老北京杂院里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市井气味迎面扑来。《城南旧事》是一部回望历史深处的作品,市井风情徐徐展开,烟火气味浓重。熙熙攘攘的前门大栅栏、古城旧街上的四合院、甚至民居的石狮子、下马石、月亮门,悠然入耳的京戏、琴书、京腔长吼、北京方言,种种老北京的影像符号都营造出一番市民生活的雅趣和闲适的胡同情调,展现了一派闲静逸乐的世俗风貌。 表现当下市民生活的电影《我的九月》生活气息浓郁,用长镜头将庸常生活邻里间的寒暄与短长、北京人的喜怒哀乐一一呈现。相类的《瞧这一家子》、《卡拉是条狗》等发生在胡同、杂院里的市民故事,也纷纷呈上长于神聊又闲情逸乐的胡同居民的形象想象,表现了京人在世情琐细中达观自足、闲情逸乐的生活美学和京都小民苦中作乐、冷眼对世的幽默传统。这些电影不仅是对京城市民经验世界、价值观念的体现,也在市井里巷的镜头下表达了城中人对城的文化认同。 北京的传统城市构形,例如主要建筑四合院,和乡土民居相类,决定了北京的空间构形在一定意义上近于乡土和自然,远离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特征。这种形状规则和向心性的城市布局易于产生文化的同化力,使城中人获得安全平和的感觉。牟复礼在《传统中国文明中的城市》中有“中国城市是‘城乡连体’”的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传统中国城乡文化连续带,北京则将这种城市和乡村密切的联系一直延续下来。费孝通所言的“乡土特色”也可对照传统北京的社会文化结构,北京的传统社群生活模式没有鲜明的城市特征,“乡土”的文化底色内在于北京的社区空间内,且存在着稳定性。电影对北京城中人的文化想象传统也集中在表现其凡俗生活、庸常世情和逸乐闲趣上。 城市结构不仅划定了日常生活空间,也在潜处影响着想象空间。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飞速发展,荧幕上涌现了一批以城市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以、改革开放后城市急剧变革和和迅速变化城市人生活、思想观念为内容。以《顽主》为标志,电影视域里北京的城市形象开始苏醒,时代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碰撞成为了新的想象维度。《夕照街》、《珍珍的发屋》等是普通人嬉笑怒骂、琐碎细小又平易温情的日常生活;也有《警察故事》、《找乐》等影片对城市变迁、现代化的回应和想象。这些电影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勃发的城市意识,证明着北京的现代化,传达新兴城市人的文化体验。 随着社会的转型,城中人的面目逐渐分化各异,电影也开始想象新类型的城市面孔,如王朔作品改编电影中的玩世流气、三两为伙的城市青年;《北京,你早!》里的新兴阶层——个体户、白领、倒爷 ;或如《夏日暖洋洋》里的都市漫游者。在城市极具膨胀的过程中,人们对逐渐熟稔的城市陌生甚至失语。此时,我们所见的北京影像也从市井生活剧转而为“都市奇遇式”的喜闹剧,在极具现代城市特征的影像中看到的则是北京市民阶层骨子里特有的玩世、仗义、戏谑和幽默。 此后,冯小刚在电影《甲方乙方》和其他作品中都延续着一种“顽主”式的情绪。城市影像也产出更多以新北京人为对象的作品,北京沉淀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又兼收各种外来思潮和文化,杂糅交织成多元的城市文化生态。北京人也因此成为多元思想文化影响下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群体,决定了城市映像关于“城中人”的想象越发众声喧哗。 城市和社区结构的变化也刺激着老北京市民的文化感情,由此诞生了一些试图拼凑、寻找老城灵魂的影像,如《剃头匠》,在电影里完成文化坚守和重组,是在城市化浪潮中对乡土北京的一种复归。导演宁瀛也试图通过《找乐》里退休老人唱京剧的故事回忆“在中国已持续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 、 三 城与人:“第三只眼”的文化记忆 早在二十年多前,作家萧乾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指向北京快速城市化、旧城市景观不断消逝的现实。 当曾有的四合院等社区单位和老建筑逐渐消逝,城市文化生态被改写,要保存本土的文化想象,电影起着重要的载体作用,它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在不断变化的文化生态下承继文化里最本质的京腔京味。宁瀛从1990年代初开始拍摄的“北京三部曲”与北京的城市改革几乎同步,其动机就起于城市的变化“人的记忆和城市的建筑、一砖一瓦是联系在一起的,砖瓦消失,记忆也不在了,城市像是从家园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 城市电影不仅通过“城”和“人”完成空间构形和文化构形,也是城和人关系的镜像。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城与人关系进行阐释“人们有的活在并消融于城、与城同体作为城的有机构件,也有的居住的同时思考着城,也思考估量着自己与城的关系,这城才是人的城。前一种人使城有人间性格,后一种人则使城得以认识自身,从而这城既不只属于它的居民,而作为文化性格被更多的人所接纳”,赵园将城与人阐释为“亲密又非无间”“富于幽惯感的对峙与和解”,但是城中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象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电影作为第三只眼,记录了城与人的相互关系,捕捉和想象城的文化性格,再现人的文化模式和人对城的文化认同。 过去的故事、彼时的社会语境塑造了这座城的想象,也塑造了人对城文化记忆。《城南旧事》从孩子的视角讲述发生在古城的往事,这部诗意之作充溢着旧日街头巷尾的市井风情。《顽主》等电影所呈现的90年代改革开放城市生活图景也是整个古老中国改革进程的缩影。《找乐》的主角是一群赋闲的北京老人,导演借助其视角“用老人步行的角度来看北京的旧式社区”。这些影片通过对城市的想象也完成了对北京社会历史空间的呈现,银幕形象成为社会形象的有力补充,共同完成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标识。 电影是乡土北京的文化记忆,而在现实的向度里,北京却在走向国际都市的大路上遭遇了很多“现代性”问题,大量人口涌至,城市充斥着大量外乡和异国的新移民,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人口密度增加、人群异质分化的……电影也对北京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弊病”做了“现代”想象。 城墙、胡同和四合院逐渐消逝,京腔、京韵日渐喑哑,城市建设进入“建筑时代”,电影开始表达多角度的北京想象,融入城市、寻找身份标识的外来人群或边缘人群成为都市影像的新内容。 80年代末期的《本命年》讲述了一个城市底层青年在重新融入城市生活却终告失败的故事,以悲剧结局表达了个人在城市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下的被放逐和无力感。这是北京市民在城市大潮中的迷失,而《头发乱了》、《北京乐与路》、《十七岁的单车》、《开往春天的地铁》讲述的则是怀揣梦想的青年在全球化时代,在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生存境遇,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充满未知威胁的巨型都市开始、或已然取代了人之城:一个为历史、记忆、人情所铭记、标识的城市”的过程中来到北京,在现代都市中迷失、打转,试图融入而不得,经历着“内在的流放”。 在此类影像中,宁瀛的“北京三部曲”(《找乐》《民警故事》《夏日暖洋洋》)尤为突出。“我虽然生长在北京,但当我对这座城市怀旧的情感发生动摇的时候,我只能在这组城市里寻找另类感,寻找陌生感,与其说是纪录了今天的现实,不如说是表现了这座城市正在让我产生的陌生感”,宁瀛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在意大利学习电影理论和创作,文化的归属感和师自欧洲电影的“纪实”手法,赋予她独特的想象方式。“北京三部曲”中的《找乐》是北京城祖父辈的故事,《民警故事》将镜头对准父亲一代,《夏日暖洋洋》则关注北京儿子们的精神困境。其中,人与城的疏离感在《夏日暖洋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影片通过出租车司机德子在都市里的漫游和苦涩的生活境遇,“在纪录片式的叙述/影像规格与个人/作者的视点和观照之间”,表达个体“即便是把出租车的车速打到极限,你能追赶上这个时代的变化”的疑问。 不论是怀旧影像中的北京还是当下大都市人的迷失、融合的故事,城市电影共同构成北京的城市电影镜像,表达人对城的文化记忆与想象。 四 “乡土”和“现代”交融的北京想象 在西方的城市研究中,“城市和乡村”对立的研究视角影响最为深远,城市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载体,负载着超出乡村及其文化的东西。如前文指出,北京的社群结构决定其城市形态异于西方现代理论里的现代城市,甚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让人生疑:它是否属于西方理论谓之的“城市”。但是,研究北京的文化特性却可以参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视角,从北京的乡土性和现代性切入。 北京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古都,如前文分析,北京在城市构形、社群结构上具有乡土特征。相比上海的个性鲜明,北京作为城市的电影想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模糊和不确定的,它被塑造为富有乡村特色的田园都市,被排除在城市之外。这种乡土感来自深层的文化意识,北京提供给居住者共同的“文化乡土”的想象,被寄予“精神故园”的文化感情。这种“文化乡土”的文化经验,是人与城间的文化同构,是人与城文化气质的契合,具有不随变化的城市形态而变的稳定性:不论这座城市变得如何现代,它作为“文化乡土”的想象也不会失落。 同时,这座城的现代特征愈发鲜明,世界大都市的表象、现代城市的景观、都市人的生活经验无不是北京的现代语境和全球视像的有力证明,它是一座“变化之地”,是一座“梦想之城”,无数现代人来此冒险,以期收获更好的城市生活,由此催生了城市电影丰富的“现代“想象。而这种现代经验,又因为城市内在的“文化乡土”底蕴不断遭受时间和空间的焦虑。 现代大都市叠加在千年古城之上,带给北京城丰富的文化复杂性,塑造了它深刻和复杂的文化性格。现代想象与历史想象在这座城里交织,催生了这方土地瑰丽多彩的城市镜像,折射着城中人悲欢苦乐的城市生活。 北京是一座乡土的城,又是一座现代的城,它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地感性化、肉身化了。北京不同于摩登繁华,堆积着各种现代符号的上海,也不同于中西合璧,萦绕着国际大都市想象的香港,它是“一个历史的想象和现实的想象相互交织的结果”。在电影视域里,关于它的乡土和现代想象,始终是互生互融的两个向度,共同塑造着这个城市的文化想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