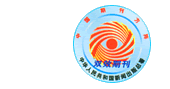大数据监管证券欺诈行为的法制完善 |
||||
|
作者:许凯 责任编辑:sxs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期:2019-11-13
|
||||
|
|
||||
|
运用大数据技术改革我国证券监管方式是新一轮证券体制变革的重要题义,2018年8月31日,中国证监会印发《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将证券监管科技的改革区分为1.0、2.0、3.0三个不同阶段,明确五大基础数据分析能力、七大类32个监管业务分析场景,提出了大数据分析中心建设原则、数据资源管理工作思路和监管科技运行管理的“十二大机制”。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方式已经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过渡之旅,大数据监管科技的实现不仅体现了与金融科技的互融互通,更是证券监管机构应对日益复杂的证券欺诈行为的“亮剑之举”。 传统证券监管方式 存在不足 证券欺诈行为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地实施扰乱证券市场正常秩序、侵害其他证券市场参与人的不法行为。依据我国现行《证券法》的规定,证券欺诈行为可以分为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虚假陈述和欺诈客户四种主要的类型,其中除了欺诈客户以外,其余三种证券欺诈行为的对象均是整个证券市场和不特定的投资人。正是由于证券欺诈行为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的扰乱结果,我国《证券法》明确了证券欺诈行为可能导致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证监会配套发布了《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等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配合出台《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司法解释,这些法律法规形成了我国现有的反证券欺诈法制体系,在实践中起到了较好的威慑和规制效果。 但不得不承认,由于证券行业高度专业化的特点,证券监管部门的行政监管、调查以及处罚是反证券欺诈法律规则发挥功能的入口,司法机关在刑事或者民事赔偿案件中对于证券欺诈行为的认定,一般也需要以行政机关的前置认定和处罚为依据。有鉴于此,证券监管成为了遏制证券欺诈行为、追究不法行为人法律责任的关键环节,而传统监管方式也为广大证券投资者所诟病。首先,传统的监管理念过于强调行政色彩,对于证券行业组织、自律组织的监管途径运用不足。这一方面导致了证券监管机构不得不独自面对浩瀚的证券市场和真伪难辨的交易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监管数据无法覆盖全市场和全流程,监管的效率和准确率势必大受影响。其次,传统监管主要关注于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对股票发行的审核、对证券欺诈行为的处罚是其核心内容,而实时性的事中监管则往往付之阙如。事中监管缺位的直接后果便是,当市场上出现证券欺诈行为苗头时,证券监管机构无法及时监测、反馈、预警相关的交易风险,等到行为危害后果显现之后再进行查处时,投资者的损失往往已经发生且在一定程度上无可挽回。最后,传统的监管方式过于依赖人为的力量,这并不是说没有数据监管的介入,而是在深度运用、挖掘数据潜力方面力度欠佳。由于数据分析和利用能力的限制,人力为主的模式使得监管成本过高,同时人力监管的随机性也难免使得证券欺诈行为的查处挂一漏万。 大数据证券监管具有时代意义 所谓大数据监管方式,其并非全盘否定、摒弃传统证券监管方式的另起炉灶,而是一种强调数据引领、全网覆盖、实时监控的辅助模式。以证监会监管科技3.0为例,它的制度核心是建设一个运转高效的监管大数据平台,综合运用电子依据、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围绕资本市场的主要生产和业务活动,进行全方位监控和历史数据分析,辅助监管人员及时发现市场主体涉嫌证券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 大数据证券监管方式的落地,既是我国实施大数据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监管机构主动对接数据科技、应对新型证券欺诈行为的有力举措。与传统监管方式相较,大数据监管的规制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现监管数据的深度利用,大数据监管并非数据的简单叠加和累积,其实质是通过构建大数据模型的方式,采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数据的智能分析和挖潜,从而解放人力,改变工作重心,提高证券欺诈行为的监管实效;二是实现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根除以往信息分散、多头监管的顽疾,以中央监管信息平台的建设为目标,实现跨部门、跨行业精准数据的全面共享;三是实现市场主体的全流程监管,尤其是在事中监管方面,通过数据归集与监测模型的建立,构建全面的风险指标体系,实现对市场主体经营过程和市场总体运行情况的有效监控。总之,大数据监管方式旨在充分发挥智能与科技的合力,打击证券欺诈行为实施者的侥幸心理,同时也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提供及时有效的预警信息。 大数据反证券欺诈机制的 法制支撑 据证监会发言人介绍,截至2019年4月26日,证监会已经公布了40宗违法违规案件,这反映出大数据监管证券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系统性威力。在为大数据反证券欺诈机制鼓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的法治要求,这一监管机制的构建与实施应当遵循法治的轨道进行。笔者以为,要为大数据证券监管提供全方位的制度保障,必须从证券立法、司法和执法三个维度展开思考。 《证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重点是根据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试点的进展情况,增加关于科创板注册制的相关规定。发行注册制的改革,其本质是放松证券领域的事前监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事前监管的弱化也会降低证券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门槛,因此强化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必须同步而行,故大数据监管方式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应当在《证券法》修订中得到明确。具体而言,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中应增加“依法采用大数据方式监测并防范、处置证券市场风险”的规定,在有权采取的措施中可纳入“电子数据取证”的内容,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中应明示“建立大数据监管平台”的制度目标。 在司法层面,此前的证券类行政案件中曾出现过证监会以“证券交易监控系统数据”为证据的情形,一时间引发司法实务界对于大数据证据性质的热议。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大数据证据应当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大数据手段获得的电子数据证据,这些数据证据虽然依赖大数据方式所获得,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证据电子化的性质。电子证据在我国修订后的三大诉讼法中均明确为独立的证据类型,因而其在诉讼法上的证据地位不存在争议。第二种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获得的分析报告,此类报告的基础来源于海量的电子数据,但与电子证据不同的是,这些报告往往是借助一定的机器算法运算形成的分析结论。对于这种大数据报告,现有的诉讼法并未作出独立的界定,但在证券类案件中却常常被用来证明或抗辩证券欺诈行为的成立、投资者损失的计算、行为与损失间因果关系等事项。基于此类报告的专业性,将其归类于鉴定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做法,这样既可以引导司法人员采取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认定证据效力,同时也能通过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等方式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在证券监管的执法领域,由于电子数据天然所具有的易篡改性,因而需要从数据收集和分析两个角度规范监管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确保大数据证据的真实性。一方面,转变为执法依据所依赖的数据必须是完整和全面的,而用以处理数据的技术、模型或算法也应当是普遍认可的,这样的大数据分析结果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和科学性;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对涉案数据的取证、保管、移送等步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或相关规定的程序进行,形成全程留痕的证据链条。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在监管数据的收集、利用、公示等方面,还必须合理限定大数据监管和个人数据保护之间的边界,防止过度监管给个人信息带来的不当损害。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