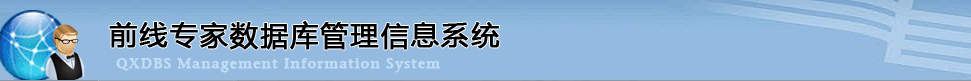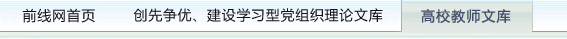|
| 重建正义与自由的理想——沉重悼念罗尔斯先生
|
| 作者:万俊人 日期:2012-12-30 阅读:1441 次
|
这是一篇我并不想写却又无法不写的纪念文章,笔同心铅一样沉重,思与言像雪无声飘扬。我要写的是我有幸在合佛大学访学期间拜识、而现在却倏地永远失去的哲学大师——约翰•罗尔斯先生!
十多天前,也就是罗尔斯教授逝世的第二天,我从哈佛朋友的来电中惊悉罗尔斯教授逝世的消息。三天后,《财经》杂志约我写了一篇两千五百字的悼念文章。篇幅之限,不得不使我欲言又止,心中的诉说冲动转向无言的回忆。感谢《文景》杂志社,让我又有了一次诉说的机会!这已经是我第二次为同一位哲学前贤的逝世撰写纪念性文章了。就在刚刚过去的上一个冬天,也是应《财经》杂志之约,我为诺刘克教授的逝世撰写了一篇不足一千五百字的记念文章。尽管我因难以控制的心情硬着头皮写出了两千字,可怜的编辑还是因其无法改变的版面约束而将文章压缩到了一千五百字以内刊出,从此留给我一份无法排遣的遗憾。今年七月,我得以重返哈佛,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访学,期间读到诺齐克教授生前的最后一部绝作《不变者》(Invariances),就此以《不变的是信念》为题,写下了一篇近万字的文章,交《读书》杂志。该杂志的朋友电话告诉我说,该文将在二○○三年第一期上发表。未曾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又不得不重复同一种写作方式,不同的是为了另一位我所熟悉和敬爱的哈佛哲学导师。
一、罗尔斯与“哈佛哲学”
确实,这又是一个让哲学界、尤其是让哈佛哲学系低首长叹的寒冬!刚刚过去的冬天,也就是今天一月二十一日,哈佛哲学系痛失诺齐克。对于总是等待“黄昏起飞”的哲学之鹰来说,还不到六十四岁的他便停止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作为哲学家的生命,实在是太早太早。而时光刚刚流逝十个月零三天,也就是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二岁的罗尔斯老人又在这隆冬季节撒袖而去,不禁使人长叹哈佛哲学的天殇地痛!是啊!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与她的荣耀常常是同她的某位或者一批独特而杰出的学者联系在一起的。“哈佛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学术共同体的标志,是因为她曾经拥有过詹姆斯、怀特海、奎因、罗尔斯等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宗师。人们不会忘记,正是由于詹姆斯创立了实用主义这一“美国本土哲学”,哈佛便因此成为了美国哲学的发源地,“哈佛哲学”也因此成了“美国哲学”的代名词。而“哈佛哲学”之有当今作为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之堡垒的荣耀,则是因为她拥有了罗尔斯这样卓越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伦理学家。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性格迥异、见解互竞、却又共享宏大学术志向的自由思想者和政治哲学家,包括普特南、阿玛蒂亚•森、诺齐克、卡维尔、斯坎伦等一连串响亮的名字。
罗尔斯对“哈佛哲学”的贡献是独特而巨大的。著名学者康马杰曾经谈到,由詹姆斯所开创的“哈佛哲学”实际代表了现代美国的哲学传统,甚至集中表达了“美国精神”的精髓,这就是:注重自由社会的价值理想和自由个性,崇尚实用技术理性,关注现实生活意义问题。这一传统曾经一直主导着哈佛哲学的走向,即使是二十世纪中叶分析哲学在西方如日中天的时候,以奎因为代表的哈佛分析哲学家们也未曾遗忘和丢掉过这一传统。迄止今日,以数理分析见长的著名哈佛哲学家普特南,甚至直接转向了重建詹姆斯哲学的哲学事业。然而,二十世纪前中期的整个西方哲学环境,毕竟对哈佛哲学的传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以至一度使得包括政治哲学和伦理学在内的“实用型”哲学传统,不得不淹没在风起云涌的分析哲学的浪潮之中而难以彰显。更为严重的是,分析哲学中激进的“科学实证化”主张,对诸如政治哲学、伦理学这类规范性哲学分支的“科学”特性和知识身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之陷入严重的知识合法性危机。面对这一局面,正是罗尔斯力拒狂浪,拯救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现代生命。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和磨砺,罗尔斯剑出清风,一部六百余页的《正义论》有如石破天惊。当代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感叹地说:《正义论》是一部具有“轴心转折”意义的巨著,她不仅恢复了道德哲学的知识尊严,而且也开创并证明了一种崭新的规范伦理学类型——现代民主社会的自由正义之制度伦理学。另一位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牛津大学的资深教授翰普歇尔评论说,《正义论》“强有力地扭转了”二十世纪“英语世界”的哲学发展方向,使英美、乃至整个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和规范伦理学得以从半个多世纪的沉睡中苏醒,继而迅速复活并达于繁荣。
的确,罗尔斯创造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奇迹:平生第一部哲学著作问世,即产生扭转乾坤、开创繁荣的划时代思想效应。更重要的是,这效应不独是学术理论的,而且还有社会实际生活的。在学术上,《正义论》的刊行迅速引起全球性的反应,在最初的十多年里,有关?书的评论或研究论文几乎每年都在两千篇以上,以至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巴瑞教授感慨不已。把这一学术景象称之为“罗尔斯产业”。在现、当代世界哲学领域,大概只有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极少数几位哲学大师造就过如此繁荣的哲学学术产业。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罗尔斯的正义主张也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他的研究,正义问题很快就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有关政府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公共论坛主题,并对相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度影响,至今依旧强劲。
这是作为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罗尔斯的人格荣誉,更是“哈佛哲学”的学术荣耀。它很自然地让人想起上一个世纪初的詹姆斯。如果说,詹姆斯以其实用主义的哲学创造而开创了美国本土哲学的先河,从而在使他本人荣获美国的“哲学爱国者”称号的同时,使得哈佛哲学系成为了美国现代哲学的摇篮的话,那么,罗尔斯则以其社会正义伦理的重建而扭转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方向,创造了哈佛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辉煌,从而在为罗尔斯本人赢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之一”的同时,也为“哈佛哲学”增添了灿烂的一章。让哈佛这所世界知名学府感到荣幸的还有,这位沉默寡言、平生述而少作的“苏格兰哲学绅士”(当代著名法学家哈特语),没有辜负哈佛的慧识与期待。他不仅是一位真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理论大师,而且也是一位睿智慈慧的大学良师。几十年来,罗尔斯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优秀人才,当今活跃于英美乃至西方学界的许多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学者都出自罗尔斯门下,其中像科恩、斯坎伦、科丝嘎德等都已然成为这一领域的名家高手。在哈佛,罗尔斯教授的课程虽然不一定是讲授得最精彩动人的,但却总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我曾经有幸聆听罗尔斯教授讲授的《西方道德哲学史》和《政治哲学》等课程,亲眼目睹了哈佛学子对这位大师的尊敬与爱戴之情。几乎是每一次罗尔斯教授讲课之后,学生们都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欢送教授离开教室,直到他听不到掌声为止。这一动人的场景无疑是对作为哈佛教授的罗尔斯先生的最高奖赏,它比之罗尔斯先生所荣获的哈佛“校长荣誉讲座教授”——据说,整个哈佛大学仅有八位教授获得这一殊荣,而迄止上世纪未,整个哈佛大学荣获诺贝尔奖的教授就已经超过三十位——来说,更让先生感到欣慰和荣耀。我曾在与罗尔斯先生交淡时,就此斗胆问过他本人,先生回答说:“万,你知道这是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情。只可惜,今年是我最后为哈佛的学生上课了。”我想,能够聆听先生的讲课是幸运的,包括我这位来自东方的访问学人。哈佛大学和哈佛哲学系更为幸运,能够得到这样一位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足以让哈佛为之骄傲!让“哈佛哲学”为之自豪!
二、重建正义伦理
罗尔斯一生的著述并不多,其中堪称代表作的有两部:其一是一九七一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正义论》;另一部则是一九九三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严格地说,前者已经成为一部社会(制度)伦理学的经典文献,后者则堪称一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的哲学教科书。然而,两者既相互区别,又一脉相承,在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知识地图中,如同双峰比肩,千秋并垂。
作为罗尔斯的成名作,《正义论》的成就非我所能品评。但我相信,该书非凡的理论成就首先缘于作者对现时代社会生活主题的深刻把握,缘于该书理论主题与社会时代之思想主题的深刻对应。经历过失去手足的切身之痛和天生体弱的少年生活,经历过太平洋战争的腥风血雨,更重要的是,亲眼目睹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风起云涌,诸如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反越(南)战的游行示威、以及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反不平等的社会风潮,罗尔斯明白了哲学的真正使命和学术责任,理解了社会弱者或者用他的术语说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和他们的基本吁求,理解了现代自由社会,包括它的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真实意义。因此,他崇尚严密高深的学理逻辑分析技巧,并且娴熟地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哲学思辩,但他不能容忍哲学对社会现实吁求的熟视无睹,不能容许自己的哲学对眼前生活世界的乱象袖手旁观。总之,在大学讲坛与生活世界之间穿梭往返的哲学家罗尔斯,不能容忍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无动于衷,甚至是无情冷漠!在罗尔斯看来,哲学首先是生活之镜和社会之道。
在现代世界里,一个非正义的社会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正义的秩序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罗尔斯所关注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建立社会正义的理由,不如说是建立社会正义的方式,这是他的正义理论所要解决的基本课题。罗尔斯首先把正义看做是一种社会基本制度的伦理价值。《正义论》开宗明义地宣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第一美德一样。”所以,一个合理可欲的社会必须是按照基本正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人类共同体。问题是,人们是先确立正义的基本原则,然后依照该原则来建立社会?还是先有了社会,然后再寻求某种社会普遍认同并遵守的正义原则?罗尔斯改造并利用了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哲学理伦,尤其是近代社会契约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和论证。按照他革新了的社会契约论思路,社会的建立与正义原则的确立是同一社会化过程的产物。在近代社会契约论者的理论中,比如,在霍布斯、洛克的理论中,正义只是人们协调利害关系而人为制定的诸多行动原则之一,是人性自私这一天然事实前提下被动产生的消极的政治伦理产品。罗尔斯以为,这样的解释并不合乎现代民主社会的实际。建立社会的目的当然是因为社会地生活比单个人孤独地生活更为有利,譬如说,更为安全、更多福利、生活更为丰富,等等。但是,要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仅有实际利益的考量并不充分。社会需要人们之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竞争。而社会一旦产生,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实际功利,哪怕是功利主义者所说的那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必须是兼顾效率、公正和秩序的民主社会。当现代社会已然找到创造效率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当效率已经不再成为现代社会的疑难问题时,社会公正就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正是如何达成基本公正的问题。在此情形下,正义就不只是消极的,同时也具有积极的社会规导作用。考虑到这一点,罗尔斯提出并论证了他的核心理念“公平的正义”,将她视之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础和理想。
“公平的正义”必须是普遍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社会正义制度化,成为具有普遍有效规范作用的基本原则。但是,人们对正义的理解并不相同。柏拉图的正义秩序显然是一种具有严格社会等级规定的秩序,即先天禀赋不同的社会各阶层各就其位,各安其所,如此即为正义。这是一种贵族式的民主正义,与之类似的还有现代精英民主的正义主张。罗尔斯反对这些主张。他坚信并坚持的是一种平等的、甚至是“平均主义的”正义理念和理想。人们在建立并维护社会生活秩序时,当然首先要确立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也就是基本自由。这是正义的第一原则,也是建立社会正义秩序的前提。其意味类似于“产权”之于公平交易的在先性。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不用说公平的交易不可能,就是最起码的交易也难以成功达成。在无法辨认交易的主体之间,难以发生交易行为,就好像两个相互模糊的商人无法成交买卖一样。所以,罗尔斯把基本自由人权看做是宪政自由,是必须首先通过国家宪法来确认和规定的基本权利。
然而,仅仅确立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罗尔斯不同于近代以来大多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主要之点:先定的宪政自由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它最多只能提供一种类似于机会均等的初步的社会制度安排,而不能保证长远有效的社会“基本善”(福利)的正义分配。由于人们先天禀赋的不同和后天诸多偶然因素所致,即便是有相同的机会,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差异,甚至是巨大的社会差异,如同从同一起跑线起跑,竞跑者们也不会同时抵达终点线一样。这是由于,“公平的正义”不仅有赖于机会均等的前提供应,而且还有赖于人们把握所予机会的能力、幸运程度、天资天赋等因素。况且,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已经处在十分不同的生活境况中,其各自所拥有的生活基点互有差异。所以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其实已经不再是机会均等一类的前定条件问题,毋宁说是如何缩小差别、重新调整利益分配的校正正义问题。看到这一点,罗尔斯大胆提出了他的第二个正义原则,也就是他所谓之的“差异原则”。如果说,在正义的第一原则中,自由的权利优先于平等的权利,那么,在正义的第二原则即“差异原则”中,情形恰好倒过来:平等的要求要优先于自由权利的要求。用罗尔斯自己的表述来说,就是:社会制度应当这样安排,以使它最有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少数弱者,人们俗称之为“惠顾少数最不利者”。在西方自由社会,这一主张是极不寻常的。它甚至隐含着某种干预、或者至少是限制自由人权的危险。实际上,像哈耶克、诺齐克等激进自由主义思想家就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指控和批评。
然而,罗尔斯的主张并不只是一种社会的伦理吁求,而是基于一种审慎理性的思考所得出的社会制度伦理结论。他援用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思想资源,论证了他所主张的“最低的最大限度规则”:即,一种以最低程度为基准的权利分配规则,将最有利于该社会中那些生活状态最接近这一基准线的群体。为此,社会在确定了原初的正义安排之后,还必须实行社会“基本善”的再分配,甚至是多次分配,以便把整个社会的善(权利)分配状态调整到能够为尽可能多的人所能容忍和接受的状态。与正义第一原则(自由平等原则)不同,正义的第二原则(“差异原则”)不是在无差别的情况下达成的,而恰恰是在有差别的情况下,并且是为了缩小差别而确立并运用的。如果说前者的无差别需要通过诸如“原初状态”(即社会的起点状态)、“无知之幕”(即所有参与社会建立的人都放弃他们各自对自己的差异性、独特性的申认和诉求)等契约环节来达成的话,那么,后者则需要借助于已有的各种社会基本制度和部门管理方式来实现。我曾经就此向罗尔斯教授本人提出过一种看法,认为他的正义第一原则仍然属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的政治主张,而他的“差异原则”实际是一种通过正视社会差异来缩小、甚至克服差异的社会伦理主张。罗尔斯先生若有所思地给了我一个简明的回答:“也许,政治的正义与社会伦理的正义原本就是分不开的。”对于当时仍然十分担心“道德政治化”风险的我来说,这一解答还显得有些费解。但不久读到罗尔斯教授的另一部新作《政治自由主义》,我才幡然大悟。
三、走向政治正义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基本上把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归类于一种社会规范伦理,甚至把它看做是一种现代性的“正义制度伦理”。我自己也这么体会。在我的体会中,重建一种社会正义(制度)伦理,既是罗尔斯孜孜以求的理论目标,也是他作为伦理学家的一种社会良知的表达,其中不仅包含着作为学者的他对现代社会生活和价值精神的深刻理解,也包含着作为伦理学家的他对现代社会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厚同情和关切。
但是,这样一种社会正义伦理仍然遇到许多理论挑战和实践困难。比如说,社会或国家用以限制个人自由权利的理由是否合法正当?国家或政府凭借什么样的理由来调整社会的制度安排、改变社会的制度分配才是正当合理的?平等的、甚至是平均主义的正义再分配在惠顾社会最不利者群体的普遍公平要求时,是否会损害另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或福利?难道只有达到这种人为平等的制度安排或社会分配才算是一种“公平的正义”吗?这种平等的正义是否会严重伤害现代社会的效率追求?而且,在现代文化多元论的前提下,一种“最低的最大限度”的普遍主义规范伦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寻求这种普遍化伦理规范的理论动机本身是否与现代民主社会的理智文化气候相适宜?如果不再依托某种道德形上学的理想预设,又如何能够确保这种公平的正义伦理达到普遍有效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以说,《正义论》出版以后的三十余年里,这些问题一直是罗尔斯面对并苦思对策的思想主题。一部理论著作引发的问题愈多,恰恰是它非凡价值的明证,而不是相反。同样,作者对其著作引发的问题所采取的学术姿态和思想立场,不仅反映着他或她的学术胸怀的宽阔或者狭隘,他或她的思想资源的丰富或者贫乏,而且也印证着他或她思想活力的强与弱。罗尔斯不愧为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更不愧为一位深邃缜密的理论大家!又经过了近二十三年的不断求索,他终于找到回应挑战和问题的良方,这就是:从社会伦理正义走向社会政治正义,其标志性理论成果是他一九九三年底发表的《政治自由主义》。
许多学人都以为,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标志着罗尔斯在理论立场上的一种退却,或者至少反映出他在思想志向上的某种后退。非常幸运,《政治自由主义》出版之初,我正在哈佛访学。拿到罗尔斯先生亲笔签名题赠的新书,我几乎是一口气在一周之内初读了全书。初读的感受与大多数学人相似。我也曾经请问过罗尔斯本人,将“公平的正义”移置并限定在政治或政治哲学的范畴内,是否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正义理论中的某些伦理理想?也就是说,这是否一种理论立场或思想抱负的退缩?未曾想到,罗尔斯的答复恰好相反。他告诉我,一种理论的谨慎并不表明一种思想的胆怯。他甚至反问过我:是把“公平的正义”定位在“政治的”层面上要求更高?还是将之定位于社会伦理的层面上要求更高?
回味良久,我才逐渐理解罗尔斯先生的良苦用心。道德与政治历来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文化生长中两个既相互紧张、又相互攀缘的基本元素。这一点,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道德一方面为社会政治提供理想的价值资源和人格的精神滋养,另一方面又对社会政治竭尽攀龙附凤之能事,借助后者的权威力量来施展其理想诉求。同样,社会政治一方面为人格道德和社会伦理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支持,以强化后者的社会规范力量,另一方面却又从道德伦理中寻求其权威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社会道义支持。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分界益发明显,前者越来越趋于人格个体化和美德心灵化,而后者则愈来愈趋向公共普适化和操作制度化。对这一事实,人们存在着两种殊为不同的感受或看法:一种看法以为,该事实表明,现代政治已然撤出甚至放弃了仰赖某种崇高价值理想的乌托邦“路径依赖”,不断走向政治现实主义。而道德则已经托付给了个人的内在良知,成为一件纯粹个人的精神事件。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另一种看法则以为,现代政治的非道德化改变或许对道德并无不益,但它会造成现代政治的实质主义沉沦,使权力事件日益蜕变为政治权宜和权力技术事件。但无论人们如何评说这一事实,都证明了道德与政治日益疏远这一事实的真实性。
罗尔斯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道德有着真切而深刻的了解。但他并不相信这一疏远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的价值沉沦后果。相反,现代政治价值的特性只会随着它普适化或公共制度规约化力量的增强而得到提升,而不是相反。因此,把“公平的正义”从社会伦理移置到社会政治的地位,也必将使其普遍化程度更高,规范化力量更强,因而在他看来,这一理论转移只能被看做是一种理论前进,而不是后退。更何况,这一转移本身并不意味着正义伦理与正义政治之间将发生任何形式的实质性断裂,事实上,它们是不可能被根本分割开来的。这是由于正义伦理本身即具有制度规约的性质,它与作为公民的社会个体的正义感和道义感相关,而与纯粹的个人美德追求无关。罗尔斯曾经含蓄地回应了麦金太尔同样含蓄的出自传统主义美德伦理的理论指控和批评,虽然他的回应本身并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
的确,当我们把“公平的正义”看做是一种社会基本政治结构的制度要求,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伦理的道义要求(规范)时,就不难明白“公平的正义”在罗尔斯心中的真实分量。他对这一基本价值理念的社会期待不是减弱了,而是提高和加强了——倘若我们理解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共化趋势及其价值后果的话。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开篇,罗尔斯就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文化多元是一个持久存在的人类社会事实,那么,在一个由自由、平等然而却又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理想和人生哲学观念的公民所组成的现代民主社会里,如何保持该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的确是现代人类和现代社会都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不仅是美国或者欧共体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比如说中东各个国家或民族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甚至也是每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而且,它也不仅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或西方世界,也属于当今几乎整个人类世界。罗尔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解答:重建公平的正义,而且是首先从社会公共政治的层面来重建公平的正义。重建是因为现代社会的正义必须是公平平等的,而不是譬如说柏拉图式的。为此,重建也必须在社会“公共理性”的层面寻求基础,而不是、也不能在任何一种哪怕是再完备、再系统、再完美不过的哲学学说、宗教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后一种方式无论如何都无法提供普遍认同的价值基础,惟有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才可能寻找到“重叠共识”,从而为建立普遍有效的社会正义秩序和正义原则开辟道路。这就是罗尔斯在其第二部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要表达的基本主题。
这一思想主题几乎支撑着罗尔斯晚年的全部哲学思考和哲学工作。一九九四年八月底,我在回国前向罗尔斯先生辞行时,曾经问过他近期和远期的研究计划。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他告诉我,他正准备花两年左右的时间考虑哈贝马斯给他的批评和建议。我知道,他指的是哈氏对《政治自由主义》的评论,和随其评论所表达的有关社会政治与社会伦理之普适主义的理论主张。然后,他将对自己经年建构起来的“公平的正义”这一核心理念和主张进行重新阐释,并对它展开范围更广的扩展性研究。我想,这就是他后来先后发表的《公平的正义——一种重新阐释》(2001年)和《万民法》(1999年)两书的初衷。而他的《论文集》(1999年)和《道德哲学史演讲录》(2000年)则是他的门下在其认可下所做的成果整理。与罗尔斯显赫的学术声誉相比,他的著述实在不算十分丰厚。然而,他严谨的思想风格和谨慎的学术姿态,已经使得他原本不多的著述具有了少见的思想深度和学术厚度,构成了当代哲学一笔难以估量的思想遗产。
四、罗尔斯及其遗产
一位真正属于我们时代的哲学家停止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生命,但他的哲学和思想的生命依然鲜活。其实,刚刚进入新世纪的人类世界仍然需要这位睿智哲人的智慧,二十一世纪的哲学仍然需要他谨慎而严密的“反思平衡”,而对于“花果飘零”的哈佛哲学系和爱默逊楼来说,他的永远离开更是一种永远的痛!
春去秋来,哈佛的学子们已经习惯了仰望星空,因为他们确信,那其中必定有从爱默逊楼升腾的哲学之星,有罗尔斯深邃而慈慧的目光。即使他们不必每时每刻与大师相随,可只要他们愿意和需要,他们便可以径直推开位于爱默逊楼二层罗尔斯教授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与他交谈。可如今,天星陨落,大师不在,他们一定会感到无法填补的巨大空虚。是啊!还有什么比失去大师更让大学和大学学子悲痛的呢?罗尔斯给哈佛和她的学子们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心痛!曾经为先生喝彩的掌声只能成为难忘记忆的回音!
此起彼伏,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之舟仿佛已经行进到了她思与言的地平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真正的智慧和真诚的智慧之爱。她曾经以其现代性的思想姿态和言说语调,对她依附既久的上帝和宗教决然地说了一声“拜拜!”,从此开始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代性(摩登)表演。然而,就在她兴致冲冲、高歌凯旋的时刻,危机与炮火教训了她的知识轻浮和思想狂妄。现代哲学的结局不幸为十九世纪末叶的尼采言中:“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可能的!”包括哲学自身的颠覆也是可能的。继而,当哲学退回书斋,刻苦寻求她自身的知识重建,并将之宣称为又一次“哥白尼革命”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离日新月异的生活世界越来越远,“摩登”的感觉显得越发空虚。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之初,胡塞尔发现了哲学的这一尴尬。他高呼:与欧洲科学危机一起发生的是哲学自身的危机,要摆脱这场深刻的危机,哲学必须“回到生活事实本身!”然而,如何回到生活世界的事实本身?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哲学一直处在彷徨之中,直到罗尔斯交出《正义论》这份厚重的答卷。罗尔斯的答卷并不全面,但它从伦理学这个曾经被称做是“第一哲学”的哲学分支入手,指出了一条哲学如何“回到生活世界”的可能的道路。他证明,正义的主题是包括现代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哲学和伦理学不可遗忘的思想主题和理论职责。更重要的是,罗尔斯用自己的睿智和慎思告诉我们,仅仅有正义的主题记忆是不够的,哲学和伦理学必须学会用新的、也就能够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的运思方式,解释和证明正义主题的现代意义和实践之途。罗尔斯让我们理解了现代社会的正义理想和正义实践。
风风雨雨,人类世界的文明之轮已经行进到了据说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新时代。过去的岁月让人类体会到了这一崭新时代的艰难、坎坷与严厉:文明进步与生态危机相伴;经济繁荣与贫困饥饿和差别歧视共存;信息网络与种族或宗教隔膜纠结;和平与大同的梦想常常被炮声和血光惊醒,“恐怖”成为当今人类难以根除的噩梦。没有人再会怀疑,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社会正义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急迫、更为显要的了。值得庆幸的是,罗尔斯的提示和探究教会了我们一种理解和把握社会正义问题的有效方式,尽管它不是惟一合理有效的方式。一位哲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足以表明哲学本身的价值了。笔行到此,我仿佛突然明白,为什么晚年的罗尔斯先生还在奋力吁求建立超越社会制度和地域文化差异的“万民法”般的正义原则,为什么还就广岛原子弹事件激扬文字(见其“广岛原子弹爆炸五十年”一文)。是啊!如果人类永远无法收敛(我不想说、也不能说“放弃”)他们对各自宗教信仰、地域文化、社会制度的过度“自恋”和执著,“全球化”将永远只能是一个虚假的相像。如果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哪怕只是以自由民主为其社会理想和名义的国度)对战争和核武器(如原子弹)的使用动机和方式,与一个比如说希特勒法西斯式的国家并无不同,人类还能有什么正义和正义战争可言?无论有多少或多么强有力的理由,美国对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罗尔斯先生看来,它已然成为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个难以消除的非正义记录。
似乎无须更多的陈述,仅仅是这种学术胸怀和思想姿态,就已经足够我们学习和领教了。只可惜,就在我们最需要他和他的思想提示的时候,他却悄悄地走了,带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也带着我们无尽的哀思……
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约翰•罗尔斯,一位不仅属于哈佛和美国,而且也属于我们大家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是真正的正义的良知和良师!
二○○二年十二月六日急就于北京西北效蓝旗营悠斋
(原刊于《文景》,2003年第1—2期合刊)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