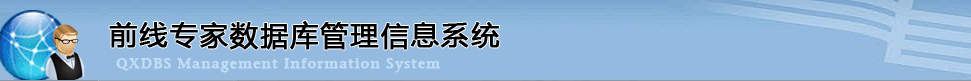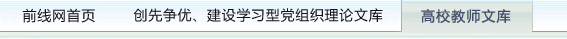|
| 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再评《全球化陷阱》
|
| 作者:万俊人 日期:2012-12-30 阅读:1332 次
|
《全球化的另一面》在《读书》(二○○○年第一期)上发表后,便受到友人和学生的质询:一说我没有把话讲完,全球化的问题似乎不只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二说我似乎有理论立场的矛盾或不统一。学生问我:“您不是倾向于支持普世伦理的么,怎么对与之相关的全球化非议得这般严厉呢?”原本只想荐述别人家的见解,到底还是未能掩饰自我的阅读主体性。
坦率地说,我确实想保持自己学术立场的中立性和连贯性,就像当代美国哲学名家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的那样“公正地看”(view from nowhere),或者如罗尔斯所说,保持一种“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为此,我特意用文章的标题标明我只谈全球化问题的“另一面”,同时又在给编辑的信中明言,即使我所谈的这“另一面”,也尚未尽言,只是由于文章写到半路已近八千文字,考虑到《读书》的编辑常规,只好中途止笔,把未尽之言留作下回分解。
未说的不是不可说的,而是非说不可的。《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谈到,全球化是一个由经济一体化表象所掩盖的“政治陷阱”,而我想追问的还有:全球化可能(但不必然)不只是一个经济陷阱和政治陷阱,而且还可能是一个文化陷阱!如此追问,不仅会将我自己的阅读主体性暴露得更加充分,而且简直就是我的评价主体性的肆无忌惮地发作了,因为所谓文化陷阱的断言并不是我的阅读文体“自我呈现”的,而是我“无所不用其极”的追问和推断,尽管我所阅读的文本(当然不限于《全球化陷阱》一书,还包括其他一些与之相关的著述)已经对此有所暗示。然而,我仍然固执地相信,这种追问和推断既有必要,也合乎理性,尤其是针对全球化这样一股非把我们大家都裹挟进去不可的巨大浪潮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别人家的事,做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但问题关乎自身,观望或迎合似不合适,需要有基本的责任和姿态。
《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几乎完全是在“风险”或“危险”的意义上来使用“陷阱”这个词的。也就是说,他们担心,一种迫使“世界上各个最富有的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更不用说其他贫弱国家的政府——引者注)都成为一种政策的俘虏”的全球化,一种以美国为“最终秩序因素”的全球化,即使对于欧洲也很可能是一场灾难。所以他们假托联合国前秘书长之口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忧心忡忡:“这是真正的危险:是一种独裁制度,还是一种民主制度将操纵全球化?”当然,他们也担心,由于地球资源的终极限制,全球化的经济构想难以成功;而因为文化多元和历史传统的地域性差异限制,全球化也极有可能成为某种乌托邦。我理解两位德国作者的忧虑,尤其是他们对全球化的政治忧虑,毕竟,他们自身的现代国家政治经验和教训给予他们太多的心理暗示:德意志民族国家是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惟一总在梦想成为世界“最终秩序因素”而终告失败的国家,他们清楚,这样一种政治现代性的谋划该是项具有多大风险的政治投资(或赌注?!)。同时,我也赞同他们忧虑全球化陷阱的基本理由: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坚强有效的保证,全球化就极可能导向单极化甚至大国模式化的经济沙文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或者说“资本国际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这一理由是足够有力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当今后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终点恰恰被人们当成了全球化时代的起点)的国际竞技场上,经济和政治都显露出被强力导入单行道的倾向:康德苏(IMF的总裁)的职责危机;安南(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和联合国资金短缺危机问题上的无奈;科索沃战争危机,以及美欧政治领袖们(或许还可加上那些信奉和追随这些政治领袖的理论家们)所大力推进的“第三条道路”;如此等等。
但是,我不愿意把“陷阱”的意义理解仅仅限制在这种消极的防御性层面,也不想只限于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我之所以还把全球化视之为一个文化陷阱,是出于这样几个考虑:首先,如果全球化不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单一的经济过程,或者易言之,如果文化要素也是全球化运动中的一个构成性方面,那么,在文化多元论已然成为或原本既定的人类文明事实的条件下,全球化能否跨越多元文化的差异分界线而达致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价值共识”?抑或,达致哪怕是罗尔斯所期待的那种“政治共识”(the law of peoples?译作“民族法”或“万民法”)?这是全球化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其次,如果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很显然,全球化就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资源短缺,而且这种文化资源的短缺是全球化自身所无法克服的。文化(我是说狭义的难以“编辑知识化”或技术化的“非科学知识”的“隐意文化”,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知识文化”)是人性化的产物,其生产方式只能靠传统的积累和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精神气质”(ethos)培育,而不可能像自然资源的加?和利用那样,借助技术的手段进行再生和模式化。真正的宗教是从民族和人们的心灵中生长出来并存在于民族和人们心灵之中的,既不可能强行制造,也不可能强行消灭,更不可能人为地创造出某种形式的“世界宗教”,即使我们可以设想康德式的“世界公民”,因为我们无法消除民族、肤色和地缘的差别。某种特定的风俗、习惯和地方性文化道德也是无法齐一化或全球化的。它们能否“转化”为全球化的资源或“支撑系统”?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除非用美国白人对待印第安原住民的那种断根式的方式。可是,断根能否彻底?彻底断根后能否毫无文化后遗症——不仅对美国人民(包括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文化而言,而且对于人类文化而言?也成问题。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现实困境可资佐证。更有甚者,《全球化陷阱》所谈到的“不同语言集团”(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语合法性问题)之间的“分延”与隔膜,也会极大地削弱全球化的文化表达力量,用时下的话说,全球化难以获得足够普遍化的话语权力,因之其信息的传播与接收便成为问题。对此,我们稍后再来详谈。最后,倘若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不仅依旧存在,而且可能还会更加严重。人们会问:一种可全球化的文化会是怎样的?谁来制定这种文化的评价标准?由谁担当这种文化秩序——假定可以建立起来的话——的维护者?
文化原本只能以人心、民族或社会(区)之精神气质为生存和生长的居所,即是说,它天然就具有无法根除的“地方性”(locality)或“区域性”(provinciality),这是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生存论意义所系。在以色列人(也许应该说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也许应该说伊斯兰民族)对耶路撒冷圣城旷日持久而又坚定不让的合法占有权的争夺中,人们应该不难明白这一点。事实上,争夺的双方都把对方的占有要求视为对自身文化信仰根基的挪用,而在他们看来(或许在所有民族看来),这种类型的挪用远不止领土占用或侵占那般难以接受,它简直就是一种民族存在理由的剥夺。以色列人可以有条件地归还给叙利亚戈兰高地,也愿意有条件地撤出南黎巴嫩“安全区”,但却无条件地坚持对耶路撒冷的拥有主权。因为耶路撒冷不是戈兰高地,对耶路撒冷的占有也不只是一个国家政治主权问题,而毋宁是一个民族文化之根的守护问题。文化主权绝不仅仅具有人们通常以为的象征意味。象征的符号或可改变,但象征符号的结构却不允许他者更换。因此有人说,耶路撒冷城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块墙砖都是一枚地雷。全球化的车轮能够趟过这片雷区么?
或曰:“为什么不能?科索沃不是也趟过去了么?”确乎,北约维和部队的坦克装甲车趟过了科索沃的边界线。但有几点需要额外特别注明:第一,趟过科索沃边界线的不仅有北约的坦克装甲车,还有俄罗斯人的坦克装甲车。两者之间虽不至于南辕北辙,却多有龃龉。这种状况本身说明,不同政治集团对科索沃事件的立场和目标并不是齐一的,更不用说全球范围的意见差异了。第二,北约的坦克之所以能够趟过科索沃的边界线(严格地说是南斯拉夫国界线),是以其飞机导弹的地毯式轰炸作为前提条件的,况且还不是趟过科索沃,而只是趟入科索沃。这种以极端政治(军事战争作为政治的极致和顶峰)强权的干预方式所实现的趟入,绝对不可能成为公认合理的跨文化差异的全球化方式。很难保证北约的这种强行闯入不是一种自陷泥淖的做法。第三,北约的趟入虽然自许人类和平和人权的名义,却并无充分的根据证明其行为的普遍合法性。而且名义上也没有诸如联合国或世界人权组织这样的组织合法性。这样的全球化只是强者的权威游戏。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北约趟入科索沃后并没有实现他们允诺的民族和解,其行为后果是,把原来的强者变成了弱者,把原来的弱者变成了强者,并且是用一种新的民族歧视置换了旧的民族歧视,半数以上的塞族人被阿族人驱逐报复,最多也只能说明北约政治权力者们所实行的民族正义还停留在《圣经•旧约》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性正义”层面,远不是他们的理论家们(如罗尔斯)所竭力论证和倡导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正义”。
因为差异,才需要正义或公正,这是经济和政治领域分配正义的道义要求。但这一原则并不能简单移植到文化领域。文化的生产是地方性和民族化的,文化的差异也不可能通过分配或重新分配来实现文化公正。文化是不可强行分配的,它只能通过不同文化系统或层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而达到相互共享。所谓文化的公正,不在于平均化、甚至齐一化的接受效果,而在于交流和理解的过程;更深一些说,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对待的主体间态度。因此它比经济和政治上的公正更依赖于人的意愿、情感、理智、判断、心理和姿态等主体性因素。这正是文化多元论所具有的一个独特特征,与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相比,其差异的内在性和不可克服性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如果《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关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陷阱而且是一个政治陷阱的分析论断是值得重视的,那么,说全球化是一个可能的文化陷阱就有更充分的理由和论据。
一些人——他们大多是我们这个世界比较有力量有权力的人,用美国人喜欢的词来说就是比较powerful的人,?仅在政治权利上,而且在话语权力上——往往更习惯于相信,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必然带来政治的普遍民主化,并且有可能期待某一种政治民主模式的全球扩展,进而最终跨过文化多元论的重重围栏,到达文化价值共识的终点。但他们似乎犯了一个简单类比的错误:印第安人发现的番茄可以全球化为现代人的大众食品,一如秘鲁人在上万年前发现的马铃薯最终成为了全球人共享的食物,这种由民族地方性到全球普遍性的逻辑似乎同样也可以成为全球化演进中的文化逻辑。可文化不是番茄和马铃薯,它们(我想只能用复数)只能交流,不能移植。当然,较为逼真的模仿和有条件有限制的分享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爵士乐或京剧,油画或水墨画,甚至是语言,等等;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像把番茄土豆种到西藏高原的现代化温控室里那样,指望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实现文化的移植或文化的齐一化。在文化的层面上,技术性操作的功效极其有限。
另一些人——他们往往属于这个星球的“第三世界”——则更容易相信,由于“不再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们是否曾经有过?),“甚至连一个共同的词汇也没有”(未免绝对?!),因而像诸如“南部、北部、第三世界、解放、进步,所有这些表述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共同意义已经消失或者死亡。这种绝望式的悲观主义对于全球化的事业来说,的确是过于恐怖了。纵然是“许多种文化带来完全不同的比赛规则”,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仍然要继续他们之间的比赛游戏。这种游戏是无法停止的,更不可能被全然取消。我们还不能对文化多元论悲观绝望到终止交往游戏的地步!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接受把最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完全排除在外或对他们毫无益处的经济全球化?还有,我们能否接受一种由某个“最终秩序因素”控制世界秩序的政治全球化?或者用《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的话说,我们能否接受用某种统一的民主商标将世界结构“连锁”(interlock)化的政治全球化?复次,一种哪怕是标榜“社会均衡原则”加“生态改造原则”、而实际上又只实践有限的集团性公正和不愿意承担相应生态保护责任的全球化是否值得欲求?最后,一种表面上承认文化多元论事实而实际上却又在竭力推行单元普世主义的文化全球化能否为各民族国家所普遍接受?这才是全球化陷阱的危险所在!它不仅仅如《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所分析的那样,造成了某种可能且可怕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并且还可能造成更令人忧虑的文化同化后果,而在我们为此忧虑之前,还必须冷静地追问一下,这种彻底化到文化根底的全盘全球化是否可能?
吉登斯说,全球化已然成为“现代性”赫然突显的当代事实,虽然他并不相信“市场经济万能论”(有时,他又将其斥之为“经济原教旨主义”)能够成为全球化的惟一通道,但他确信,一种汲取并综合左(第二、第三或者可能还有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右(激进自由主义和过度权利化的个人主义)两派思想活力的“中道”即“第三条道路”,有希望成为全球化的可行之道。无独有偶,当今风流西方政坛的政治领袖们如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以及因过于急躁和失措而提前下台的原德国财长拉封丹等人,也一再强调,全球化已不只是一种新的趋势或一个新的方向,而是一种已然的事实。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断言,“第三条道路”是惟一有希望将人类导向全球化光辉顶点的康庄大道。
然则我仍然担心,“第三条道路”仍然只是一条“单行道”(only way)。后冷战时代的西方政治家们太容易相信福山的寓言式宣言,相信一九八九年柏林墙被推倒后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结的人的历史。福山的“最后的人”是“惟一者”诞生的先声。这“惟一者”是否就是全球化大写的“人”?回应福山的是被《全球化陷阱》的作者们称之为“新的箴言”的警告:“快逃命吧!谁又能够逃脱得了呢?因为在资本主义胜利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一九八九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做‘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
这种回应在一些更富于现代理性的思想家们,比如说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看来,可能过于情绪化、过于消极。哈贝马斯坚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仍然是一个开放着的未完成的谋划,而罗尔斯则仍在一如既往地“建构”着他所坚信不移的可普遍化的自由主义。他们都承认,文化多元论是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一个客观既定的事实,但确信我们仍然可以跨越文化多元的差异分界线,达致某种形式的“共识”。罗尔斯采用了一种看似退却谨慎实则精进大胆的理论论证方式:即便我们必须放弃某种文化道德认同如正义伦理原则认同的奢望(非如此不可?!),也依然可以通过民主契约的方式,达致政治的“重叠共识”(政治正义——其国际延伸是所谓“万民法”)。而哈贝马斯则提供了一种更乐观理想的哲学论证:以某种普遍语言学和语用学的方式,建构一种公共论坛和参与这一公共论坛的“理想语言”(非私人化语言),从而通过民主对话和辩谈(商谈)抵达普遍的“价值共识”。在这里,“价值共识”的““实质性内容”是次要的,寻求这种共识的民主过程或公正程序才至关重要。
我认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论证有其合理性,如果把它限定在特定民族国家的政治范围内,比如说作为他说的那种“宪法共识”。但我怀疑能否把这种政治正义的原则推广到特定的国家政治结构以外。“万民法”固然可以作为全球化的政治基础,可它如何穿透民族文化的厚墙呢?毕竟任何人都无法担保各特殊民族能够像志愿参与缔结国家组织的公民个体那样,愿意被“无知之幕”笼罩起来而对自身的利益(权利)保持冷漠的心态。与此相比,我更疑虑哈贝马斯的“理想语言”和借此对话所达成的“价值共识”。如果这种“理想语言”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科学语言,那么,它可否用做文化对话?毕竟,由于科学知识及其表达与人文智识及其表达之间有着不可通约的特性,所以科学(人工逻辑)话语与人文(日常自然)话语以及它们各自的言述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种“理想语言”是一种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语言,那么,它又如何达成语言意义或意味的公度?在比如说英语与汉语、太平洋岛屿上原住民族的俚语与现代英语、甚至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之间,人们能够在毫无语意或语义遗失甚或误解的情况下进行理想的对话交流么?倘若不能,以公共论坛的对话方式寻求“价值共识”的期望又如何实现?
查尔斯•泰勒说,达成某种限制性“政治共识”的前提是“承认的政治”,即首先承认各不同政治主体(如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独立。麦金太尔则以更为激进的语气说,不用说不同语种(系)之间的完全翻译不可能,就是不同时期的同一语种也可能出现转换的困难(这印证了中国语言学中训诂学的工具合理性和诠释合法性),例如,同样是《荷马史诗》的希腊语文本,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三种英语译本中,就成了三种差别重大、意味殊异的现代诗。之所以如此,盖因不同语言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汇、语词意味、语句结构和语法规则,以及说语言的语境(包括由文化传统所预制的特殊语境),后者甚至影响到同一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用和语义。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是不同语言言述和对话交流得以可能的关键。也就是说,不同语言间的可译性是它们的言述(utterance,发声)可相互理解的前提。如果真的如麦金太尔(还应包括奎因,他有“不可译性原则”一说)所言,若两种语言间完全不可互译,其言说者之间的对话就无异于对牛弹琴。只有“说”“听”声响而无信息交换的对话不是真正的对话。
麦金太尔先生过于武断和悲观了。不同语言间确定不可能完全互译,原因在于,翻译本身总存在信息遗漏,我在一篇译后记中甚至自我抱怨说,翻译简直就是一种意义扼杀。但尽管如此,我也不认为不同语言之绝对是完全不可互译的,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自然,麦金太尔先生也不会糊涂极端到违背常识的地步。他曾针对我的疑惑来信说,他的本意只是想提示那些普遍主义思想家,任何想要超脱特定文化语境、忽略不同语法结构和规则之差异性而追求某种绝对价值公度的做法,都只能是一种文化梦想。由是观之,哈贝马斯先生大概又过于理想和乐观了,难怪他对以自己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为执政木铎、并把民族认同与全球“价值共识”相提并论的母国总理施罗德仍感不满,更难怪他用“道德与法边界上的战争”理由,来为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作理论辩护了。
二○○○年二月十六日于北京西郊悠斋
(原刊于《读书》,2000年第12期)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