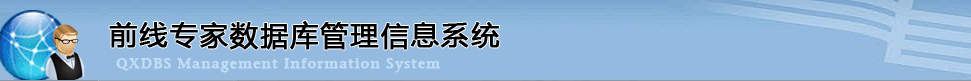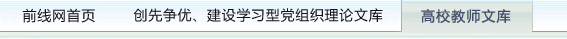|
| 后现代大众传媒的价值透视
|
|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109 次
|
信息膨胀与文化转型使哲人们断言:后现代时代已然来临。在“后”主义氛围中,当代人置身于超负荷的信息网络,日益感到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世界之间铭心刻骨的疏离。人们日益依赖于传媒手段,诸如电视、电影、报刊、广告等,以扩大个体视界和对话交流,但同时又分明感到“话语”(discourses)的不可端倪,意义的不可把捉,从而使自己日益消隐并失语于这种单向度的无回应的“交流”中。后现代信息的紊乱和超量化导致人的信息过敏症,并使其心性情怀在信息的恐惶中渐趋萎缩。
事实上,这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文化交流中断的现象,反映了这个时代感情和语言的贫乏,反映了一种没有虔敬心性,没有仪式的生命贫困。后现代文化是这个时代根本困惑的聚焦。[ 参阅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审视是当代学人在世纪末进行价值重建的—个不可忽视的基点。
传媒的“意义”:由深度到平面
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性,使人的选择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后现代文化“策略”鼓励人的“平面性”,使人终于逃离了精神价值“深度”而体味了感觉的“眩惑”和阐释的“焦虑”。随着“文化颠覆”和“感觉革命”的加剧,后现代美学张扬一种“视觉美学”,企图通过对人的感觉方式的革命,对整个社会结构、语言结构、文化结构加以颠覆,以感觉逆转的激进方式,使人对传统秩序一律厌倦而达到抗击理性的“文化狂欢”(巴赫金)的目的。
对大众传媒的分析,是后现代大师们—项重要的工作。美国社会学、文化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状况:后现代信息膨胀,使人的心理产生“晕眩感”,传统的文字信息逐渐被直观而真实的视觉画面所取代。如今,在人与人缺乏交流而退缩内心的时代,只有视觉画面可以供人们逃避无处不在的孤独,从而成为信息传播的当代方式。所以,严格地说,视觉美学是真正的后现代美学。它以直观的“在场”感,巨大的冲击力和话语诱惑力而成为后现代审美的主导潮流。电视、电影乃至录像,为当代人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逼真、快捷、直观的图像,这一方面与当代观众渴望行动、参与,追求新奇刺激,追求轰动的心理欲望相合拍;另一方面,视觉的同步性(电视现场直播、采访)可以强化感性的直接性,把观众拉入行动之中,甚至将一些充满刺激的场面和形象以特写镜头、快速推拉的方式强加给观众,从而使视觉感日渐丧失其回味和观照的耐心,而追求刺激并生产和再生产人的新欲望,甚至因艺术表现力匮乏而直接退化到震动感官的地步。这一状况无疑进一步加重了意义的消失,使人与人的交流丧失了情感和深度,仅仅退到一个画面的冲击网中。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弗•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注意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大特征是“复制”。“复制”这一重要概念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提出的。在“文化工业”中,“复制”使众多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从而使“真品”和“摹本”的区分丧失了意义,本真性的标准开始坍塌,艺术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转。杰姆逊据此认为,复制宣告所谓的“原作”已不复存在,艺术成了“类象”(simulacrum),即没有原本的摹本。“类象”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徽章,电视、电影、摄影、唱片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的生产,都是从事“类象”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注定了当今世界已被文本和类象所包围,丧失了现实感,形成事物的非真实化。而艺术作品的非真实化,以有形象、可复制的形象对社会和世界进行“非真实化”。
文化工业的复制导致现代人审美心理距离的消失。面对电视机,出现在电视上的信息失去了“它性”,“它进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后现代传媒中,所有其它传媒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68。]在这个视觉感官化的时代,摄像、录像和多媒体复制的形象文化(包括电影、电视、电脑、摄影、广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电视使人所看到的与在绘画中所看到的完全不同。人所看到的绘画作品不是现实,而人所看到的电视却是“现实”,但又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影像。由物退到物的影像,这状况被法国解构理论家所言中: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这一由物变为“物象”的过程,使得事物仿佛不复存在。当指涉物退隐时,距离感也消失了,这样,复制在使“本源”丧失的同时,也消隐了独一无二性和终极价值的可能性。一切都在一个平面的影像上,没有深度和历史,没有主体和原体。人终于被各种人造的类象包围起来,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的形象化扩张使现实本身退隐了。信息的芜杂使人丧失了思考和判断,主体在传媒的包裹中丧失了。艺术在与生活的“原则同格”中失去了意义。而电视节目尤其是引进的供消费的文化节目,则可能因忽视电视对人行为所造成的反文化效应,而导致第三世界文化价值观的混乱。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查尔斯•纽曼(Charles Newman)在《后现代气息》中,受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思想影响,认为影视文化构成后现代文化的基调,影视所再现的现实,使现实成为一种技术组织的产品,经验和想象的审美完满性、人与作品在沉思中静静观照交流的氤氲“气息”(aura)消逝殆尽,剩下的是银幕屏幕画面的强制性效果。现代电视、电影、激光视盘,以快速的切换和强烈的推拉镜头使人无法从容观照回味,画面的逼真和转瞬即逝使人放弃了回味和沉醉的审美心态,而被屏幕强制性地牵着走,从而在屏幕的“暴政”强制下,彻底放弃传统艺术独一无二的权威性,而接受新的心理效应——“震惊”(shock)。这种“气息”让位于“震惊”的心理过程,标划出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折的轨迹。在我看来,就积极意义而言,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片断化使人零散化,而影视以触目惊心的镜头打破传统艺术的自满自足的贵族“气息”,而不断修正观众的视觉和意识,并进而在视觉的重新整合中发现与日常生活碎片所拆散的生活本身的真实,引起心灵的震谅。这样,将整体分解为碎片,然后再从碎片中窥见那已然破碎而不可复聚的整体的当代本质,使人真真切切地感到动荡分裂的世界。就消极意义而言,这种对传统艺术“气息”的诀别,使艺术成为审丑和丧失精神之维的“平面”。电视、电影和录相所展示的场景和变焦、画面分割和视觉冲击使人们处身的世界时空发生了裂变:空间在变焦中变形而成为“幻觉的剧场”,时间在慢动作(或快动作中)延伸(或压缩),一切优美、宁静、精神性的东西,在现实中遭致零散化,又在艺术中遭到摒弃。艺术成了强化现实废墟和精神碎片的传媒,再也无力重建精神维度和艺术价值。就后现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看,通货膨胀是后现代文化品格的经济基因,这就从根本上孕育了后现代主义最具摧毁性特征的文化断裂。不仅如此,通货膨胀在削弱那消失了内聚力的社会中使参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浅薄和心理压力达到新的不顾后果的程度。其结果,经济和社会遭致的破坏随通货膨胀的消失而逐步走向复兴,而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却遭致了前所未有的反常性。[ Charles Newman, The Post-Modern Aura, The Act of Fiction in an Age of Infl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8.]以精神沦丧为代价换取的“欲”与“钱”,并不具有合法性。当代传媒的前景在于仍然以精神性为其内核,回归一种清新的“气息”之中,从对大众传媒时代的反省中重展健康人性和精神价值的完满性。
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从意识形态分析和大众文化批判入手,指出后工业社会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唱片和畅销书调节大众生活,控制个体生存,灌输思想,将强化的思维方式作为法则和价值标准强加给人们,在获得权力话语以控制民众的同时,使人丧失内在的自由、独立的生命意志和个体的思想判断力。影视文化具有重造神话的功能,通过复制一个个美好神奇的神话,使人们抛弃了灵魂追问,价值探询和心性匡正,而沉醉在影视文化所提供的性和暴力的“快餐文化”消费之中。
总体上看,当代世界一流思想家已经关注到人与人交流的阻绝和影视广播等现代传媒的单向“中断”作用。文化思想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一方面注意到传媒对大众消费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更注意到传媒对性与暴力的热衷所导致的否弃深度、否弃精神的感官革命的“平面模式”。这种无深度的肉身感官满足,将使后现代文化行进在“欲望占有”(弗洛姆)的文化心态中,失落在“文化转型”(利奥塔)的时空之中。
当然,尽管几位后现代大师对传媒在后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精辟分析,但总体上看仍只是理论层面的言谈,而尚未彻底进入传媒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纵深分析。真正全面深入地研究后现代传媒理论,并引起当代学者普遍关注的,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后现代文化理论家让•博德里亚(J. Baudrillard)。
交流的失效:由对话到疏离
博德里亚是与利奥塔齐名的思想家。他在利奥塔(J.F. Lyotard)考察后现代知识状态及其转型[ 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by Cr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7.]中受到启发,又在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交往理性”[ J. Habermas,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22, 1981, pp.3-14;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Suhrkamp, 1981.]理论中看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
这位颇有创建的后现代大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文化已经商品化,而商品又已经符码化。也就是说,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炒”和被关注。而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任何商品的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
事实上,大众媒体(mass media)如今重新界定着传播(communication),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
就本质而言,人们需要传媒是因为人们需要彼此间的信息交流。然而,大众传播却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只能跟着影视的感觉走,跟着广告的诱惑去选择,跟着“星”们去潇洒。传媒的介入中断了人的内省和人与人相互间的交谈。大众传播的播出是单向度的,不象对话那样有情感心性的交流回应,这种“无回应”的播出缺乏沟通,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系统”。这种不平等的话语输出,实质上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话语权力实质。传播与回应的不均等关系,使权力属于能施予而又使对方无能偿付回应的一方。当然,现实中的观者也可以转换频道或关掉电视机而行使自己的选择权,这似乎也可以算是一种回应,但这仅仅是对施予的接受或不接受而已,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力运作方式给施予者以对等的回应,就这一关键性问题而言,传播是对接受者自由选择的限定,因为说到底,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没有对答回应这种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
更深一层看,电视的确使我们与世界的距离拉近了。它通过编辑好的“实况”的真实世界,使人看得远(tele-)并更为多样地观看这个感性世界。然而,人与世界之间因为有了媒体而“远视”的同时,看的方式却因媒体的中介作用而被限定。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只要想想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就够了)。于是,媒体构成真实,媒体造成事件,媒体制造热点,媒体也忽略那些不应忽略的价值,甚至媒体也制造虚假和谎言。人们看世界的立体的多维的方式如今剥离得只剩下墙上的“窗”——电视了。人们长时间地凝视它,看的却是它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世界,一个人为的“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定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媒体成了沟通的“不导体”。
这一点无可怀疑;传媒播出的事件是打上了权力话语的烙印的。媒体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人成为媒体的附属物,成为媒体的延伸。媒体将人内化,使人只能如此看、如此听、如此想。人从接受的主体成为媒体的隶属品——终端接受器。人这种“终端机”可以在多频道中不断地调换频道,并数小时一动不动地凝视斑杂的画面和芜杂的信息。这种人将自己物化(接受器化、选台器化)的结果是,人接受储存了许多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因为人脑已被这类信息塞得满满的,人从思想的动物退化为储存信息的动物,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在这里,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异化状态消失了,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存在超越性和深度性,不再有舞台和镜像,只有网络与屏幕,只有原作的单向涉入与接受的被动性。[ J. Baudrillard, The Ecstas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Semiotext, p12; 另见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St. Louis, Mo: Telos Press.]
人们凝视电视而达到一种出神忘我的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人们借助电视、视盘、电影可以窥视他人的生活,犯罪的过程,性与暴力的过程。人们的私有空间成了媒体聚焦之所,整个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又不必要地展现在家里。尤其是那些矫情的、色情的、无情的、凶杀的、恐怖的片子,更是使人在迷醉中得到下意识欲望的满足又膨胀出更刺激的欲望。
不难看出,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的家庭化,导致了传媒(尤其是卫视)的世界一体化,从而使紊乱的信息传播全球化。[ 必须指出,电视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人们的自由时间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某地一小镇的电视转播塔被雷击而中断转播。最初人们感到生活变得失去向心力而枯燥乏味,于是,大家只得在傍晚走出家门互相拜访谈心。镇上闲置已久的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室、影剧院、体育馆和公园又重新热闹起来。人们突然意识到,这种人我交流的生活比“电视垄断”的面壁而视的被动生活方式更为丰富多彩,充满人性和富有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漠然疏远变得融洽亲密。过去单调的凝视电视的夜间生活变成了阅读、散步、谈心、听音乐会,空间由闭锁而敞开,生活由单维而恢复了多维。因此,可以认为,电视只能是生命信息交流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生活的全部或唯一。]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信息扩张和误读造成文明的误读和冲突,另一方面,传媒信息的膨胀因失去控制而使当代人处于新的一轮精神分裂和欲望猥亵的失控状态之中。
就思想价值取向而言,博德里亚对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是持冷峻批判态度的。因此,他在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中被认为是“非乐观态度”的后现代学者。在我看来,博德里亚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可以说,他在传媒热衷于制造“追星”群体和消费“热点”之中,给当代失重的人们亮出了另一种价值尺度。
价值的批判:由虚无到理想
哲人们的大众传媒批判,为我们的文化批判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有可能从文化的表层进入一种有深度意义的发掘之中。
仅仅停留在传媒的世界一体化和欲望的膨胀化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层分析传媒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传媒在消解理想而张扬消费主义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剥离大众传媒在消解政治、文化神话的同时所塑形的金钱神话的实质,使人生意义失落的真相显现出来。
当今世界,后现代主义在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时,自己却不期然地成为最具话语权力的意识形态。今日大众传媒所禀有的意识形态性,使其不再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本质虚伪性,而是不断通过极为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的生活并掩盖生活境界低俗化的真相。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消费的价值标准强加给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个人,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民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匮乏时代的金光闪闪的现代神话。
现代传媒塑造虚假的金钱神话和消费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使现实统治合法化,使生活在痛苦压抑现实中的大众,获得一种迷醉和谐的假象,通过复制一个个温馨的金钱神话或现代化神话,使人们忍受当下的精神苦闷和心理压抑,并把这种受权力话语支配控制的生活当作自由愉悦的生活,把意识的灌输和强制当作自我自觉的意识,把只重金钱的消费社会所强加于个体的控制误认为是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于是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出现了有利于统治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使人们逐渐抛弃了超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丢弃一度拥有的或追求的创造性和个体性,走向迎合潮流、唯新是求地趋向时尚。因此,研究大众传媒必须回到文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上来,才能切实地进入对文化的意识权力话语的分析批判。
大众传媒的兴起是建立在“精英文化”衰败的基础上的。当过去那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无济于世,那种狂热的政治神话在现实中露出了非人的面目时,意识形态开始转型,即由政治意识形态转向科技意识形态(马尔库塞),再转为金钱意识形态甚至消费意识形态(杰姆逊)。于是,金钱和消费的政治化与意识权力中心化一经生产出来,就开始寻求并俘虏自己的理解者,使任何抛弃旧有意识话语而认同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现代人,通过电视和广告不断强化和固化,将生活阐释成当代消费意识形态的形象解读。今天,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影视广告在制造新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压抑扩散成贫与富、奢靡与饥馁对应的新冲击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解读则必然使不同消费阶层的差异和冲突明晰化,使人类共同富裕的承诺在当下的消费巨大反差中,演绎成一种钱就是权的世界人生分裂冲突的对峙图景。而这种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却不期然地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包装所掩盖,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现代化代价与出路问题、后现代与第三世界文化发展问题、权钱交易问题、道德沦丧问题、文化滑坡问题成堆的今天,影视娱乐与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甚至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反衬出广告语言的浅薄空洞。它虽然风靡全球,但却丧失了生活的地基,反映不出任何时代的症候,它只是同义反复的重复、延伸和再现,藉此,靠自己花哨而没有规则的声、光、色的技巧维持一个空名罢了。当然,影视广告也许恰恰在以这种拒斥意识话语的方式呈现意识形态。它所渲染的生活成为与周围事物隔绝的产物,它同周遭人事相分离,钻进自己的价值空隙,然而却又在“语言的垃圾”中不断间接地提到这些周围事物。因此,意识形态以其意味深长的沉默、巨大的空隙和歧异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扭转力造成世象的一系列裂缝,使人们看到意识话语的阻隔性和虚伪性。人们看广告,似乎常常觉得效果“正相反”,上面吹得天花乱坠的同它实际上指涉的东西恰好正相反。“问题”正是在其“没有说出的话”中无意透露的。
现代某些传媒广告正在剥离人世间真情怀的温情而显示出赤裸裸的钱权交易、钱肉交易。这种表面热闹的画面其本质是将虚设的冷漠作为其性格特征。这种外热内冷的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冷漠性,并以其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显示了空隙的界限,表明意识形态同真实历史的冲突关系,从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消解,据此揭开了意识形态本身所固有的更大的欺骗性。当消费的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时,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正常的唯一意义所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
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所有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造成新的一轮话语沟涌和制约的无效,鼓励文化渎神和理想消解。于是,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并没有给人同时带来精神的充盈和信念的坚定,相反,在传媒的意识权力排斥下,真正的艺术家由精神乌托邦中退出,虚无主义乘虚而入。
在传媒所掀起的“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反攻倒算中,整个文化界改观了:消解意义而张扬欲望,反对永恒而酷好当下,弃置精神而嗜谈本能。大众文化在传媒广告的牵引下,已经从文化的价值层面向游戏层面回溯:由文化批判而形式结构,由形式结构而直觉表现,由直觉表现而对象摹仿。今日的文化写作已经抵达了低劣浅表的“挪用”、“照搬”,一种无情怀的“顺流而下”。以传媒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是一种宁要世俗不要理想,宁要欲望而不要情怀,宁要宣泄不要升华的艺术,一种反美学、反文化的艺术。这种精神价值的跌落标明理想主义已经被虚无主义所取代。当代艺术家也许有过愤世嫉俗,有过精神的张扬,但却在这旧世纪将去,新世纪将临的历史节点上,遭遇到生活法则与自由放纵的冲突,感受渴望交流与封闭隔膜的、心灵的冲撞,以及欲望的肉身对高场的精神的“翻身”。于是他们以大奇大怪、大新大异的形式去变态地表现那不可自抑的感觉之流,并以大苦大寂、大冷大凉,表现自己对世界的失望和弃绝。由传媒所代表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艺术由灵魂裸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一种放逐本真情感的“语言游戏”。这种状态只能说明某些“大众艺术”的“大腕”的灵魂分裂成两半:一半是尼采式的“超人意志”,一半是卡夫卡式的“弱的天才”性格。这种分裂的灵魂,只能使意志失去涌动的力量,使当代传媒艺术性格更为乖张而飘浮。于是,在这种文化思潮的带领下,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而对神圣美好的东西不再信任,那种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怀为虚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于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文化消解者对光明美好之物总是以阴暗之心亵渎而后快之,不仅对人自身的伟大之处加以嘲弄,而且归附一些消极被动的自卑情绪。厌倦一切精神拓展,只追求享乐欲壑的永难填平,以其很猥琐的生存作为存在的最终目的,由此形成一种自我贬损的原罪心理,在丧失活生生的生命意识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物欲膨胀的精神侏儒。而流行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浑浑噩噩生活的现世合法性,于是,流行艺术借助传媒开始了以轻浅谑浪的“侃”的文字游戏人生和世界,去掉了人们所剩无几的价值关怀,使生命升华之境开始错位,使无聊的“肥皂剧”统管了人们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时间,由那种背离了生命启迪和直面苦难的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柔甜的耳畔丝语,展开了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大众的“文化策略”。时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和稳定的审美趣味,助长不健全的好奇心和发财路径,在广告化约生活场景中泛滥媚俗的人生喟叹和唯功利的个人胸襟。而正常的文化批判被无判断的吹捧所淹没,追求一时的出名或生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
无疑,传媒所代表的新的意识形态有着很强的浸蚀性。它在给人们感官刺激中不知不觉地“洗脑”。然而在其影响下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似乎又走上玩世主义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观念上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在艺术趣味上则是超新逐俗的精神矮化。于是对理想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成为今日时髦:贬斥理想而鼓吹堕落,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感官享乐。我不认为这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不管它是披着什么样的“现代化”或“后现代性”的外衣。
如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压抑人类精神中值得珍视的那部分潜能的状况。在这个张扬形式而压缩内容,热衷能指而消解所指(意义)的时代,一切误导都神速地通过传媒传到干家万户。这种文化生产的链条不同于往昔,它已由范围的闭锁变为全球文化的把握,这种芜杂的信息和资讯传掐的全球渗透,使电视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成为个人消费和对未来策划的意识塑形,从而使媒介内容甚至广告形式都可以独立地复制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互渗共谋,并透过意识形态的允诺而运作,目的在于出售现代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观念体系,复制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种种生产关系。于是人与传媒互相刺激:媒介生产人的欲望,充满欲望的人对广告加以新的诠释。这样意识圈与经济圈所构成的恶性循环,使人被牢牢地编入广告与行销体系的运转逻辑之中。
因此,在今天,有必要更进一层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新意识形态属性,使人们重新禀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更深一层地透过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和价值关怀。
精神的定位:由消解到对话
沉醉在传媒“类象”构成的“幻觉剧场”中是危险的,同样,在“话语膨胀”中抛弃精神价值和本真情怀,只认同金钱带来的快感,而使艺术日渐向日常生活话语靠近,同样是危险的。因此,对后现代传媒及其节目制作和消费方式加以审视,在今日显得尤为重要。
后现代艺术的危机是总体性的,不仅在节目的发送方式和接收方式上,而且在艺术观念、审美心态上都发生了巨大的“话语转型”。艺术这一以个性对抗共性,以自由对抗法则的精灵,却在日益精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社会中被技术化和程序化了,从而使艺术的独立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精神被剥离并同一在社会传媒的总体性过程中。这种遭到同化的“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反过来操纵了当代人的生活体验,并逐步纳入市场的轨道,便生命体验连带人的心性情怀也打上商品的烙印。
文化的商品化和心性的边缘化,使当今杜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而以“炒”名人和名牌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那些一掷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大腕大款,在购买名牌商品时所感到的踌躇志满、所体会到的出人头地以及“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心理幻象,是以一种文化的(或变态文化的)方式对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编码。当这类大款被名牌所包装起来时,他那苍白的灵魂和空虚的大脑再也不被人所注意,人们(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少年)被这种文化的商品或商品的文化包装所“震惊”而感到一种眩惑感。这种心理的失重使其立即放弃原有的文化价值尺度,而重新对生活进行新的文化编码,进而认同这种名牌包装的人是文化强人。而今,电视和广告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名牌包装术,使人消费名牌时误以为自己具有了文化名牌的品质。对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作价值判断是容易的,然而,进行文化深层次的剖析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消费主义风行,使消费日益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塑形转成为时尚的包装,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经过名牌式的广告包装,就有被大众遗忘的危险。而真正有思想、有艺术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因缺少文化包装而默默无闻。至于现代传媒的包装术则无奇不有,诸如敏感人物和生活的曝光,明星的吃喝拉撒、所用香皂的牌子或喜欢某种饮料、文稿拍卖与竞价的新闻镜头,小说出版之前的“炒新闻”的策略等等,更是有意无意地制造“热点”,刺激“追星族”、“发烧族”的产生。文化舞台上暴露个人隐私,可以造就明星和大众偶像。于是,这个世界在镜头过度曝光中成为“太透明”时,人们便在目不暇接的图像晕眩中,丧失了判断力。于是,“跟着潮流,别落下”,已然成为当今追逐时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写照。可以说,传媒正是在制造“星”和“追星”的现代剧场,前所未有地“常态”地运行着。
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所取代,在阅读逐渐为凝视电视所转换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离画面去从独特的角度去看和听,并透过表面看到深层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人只有一种看的方式,那就是电视镜头提供给你看的方式。而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甚至不掺杂情感的。当你刚为屏幕上失学的儿童或惨遭拐卖的少女们而扼腕时,广告以夸张的语调推出的“味道好极了”或“最新马桶除臭剂”会立即使你的揪心扼腕之思失重。广而言之,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脑多媒体、电视机、收音机、报刊杂志将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塞入每个大脑。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化大众”的深度模式已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采编播人员不断根据大众需要推出千篇一律的实用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批判和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真、善、美的价值判断。大众看世界的方式凝固为小小屏幕的“窗口”,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户晓,凡是上面找不到踪影的则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无疑,这种获取信息的类像化、狭窄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导演的文化观、价值观的趋同化。这一恶性循环将意味着历史的消解和思想者的隐遁。因为,被媒体所聚焦则成为名人、名流、明星,而不被其关注,则有等于无。市场和传媒已成为存在与不存在、名与不名的场所和价值尺度。炒文化终于使文化中最可贵的“超越性”、“可能性”变成了“享受性”和“现世性”。
更为严重的是,信息传播生产的“平面”意义加速了人生重要的情怀、价值、心性、理想等本体意义的流失。当然,电视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涉,但电视内容和电视播出与消费方式却关涉意义与价值问题。当电视热衷于事件表面的喧哗和广告的竞相角逐时,价值判断和意义本位却日益萎缩。资讯在瓦解人们思想并以画面刺激人的感官之时,成功地瓦解了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寻和反思。意义的失落是资讯与大众媒体溶解消散作用的负面效应,是拒斥深度意义,增强享乐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于是,在意义消隐的终点,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大众时代”(the mass age)。这个大众时代是一个缺乏反思和情怀的时代,它通过电视只看社会的景观和场面,却不问这景观预示着什么?这一场面掩盖或暗示了什么?
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冷却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在“妙文化”的信息盲目迭加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感和刨伤,使其遗忘生活和命运的严峻性以及安身立命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识成为了电视的知识竞赛的表演,今天的大众趣味是在无目的“忙碌”中获取流行的“文化快餐”,今天的学术精英的追问意义和求索知识本质的电视节目在综艺节目这类“化解意义”的笑闹中,收视率几乎等于零。人们更乐于看时装、化妆、烹调、小品之类的节目。试想,当人们已经在消费主义潮流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钱而不是灵性精神时,感到扭曲的是知识者而不是自得其乐的自己时,知识精英的启蒙和精神重建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大众的“盲点”之中。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正在加速销毁意义的工作,这一状况应引起思想考和文化学者的高度重视。
当然,电视传播本身的中性品质,使其可以为任何人服务。出问题的不是传媒本身,而是操作传媒的人。今天,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更需深刻地认识走向现代化的代价和后现代传媒的负面效应,从而在整个传媒的流行音乐热中,在媒体的多元价值清单中,清晰地看到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人的问题、生命价值问题、乃至人生形而上问题都已得到解决,而是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空前突出又遭到空前的消解和销毁。对此难道我们还不应问一问么?
在我看来,哲人们的追问仅仅为我们自己的追问提供了一个支点,一个契机。我们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者和后现代传媒研究者都必得重视后现代学者发出的警告。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在理想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的价值归依何处?仍得追问在现代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追问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现实塑形与自我塑形?追问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迈上“化大众”的新境界。
过分的科技恐惧症和病态的“乡愁”都是需要克服的。真正的态度是深入探讨大众传播中的文化策略问题,探讨意识话语权力和接受心态的互相制约问题,探讨因传媒而加速并扩大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后殖民主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清醒而健康地面对“对话”,面对“意义”,在后现代文化转型中实现价值重建和精神定位,实现真正的多元多维的心性交。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