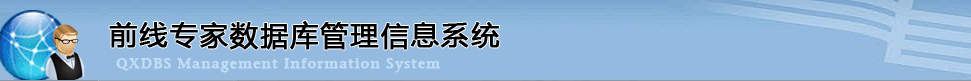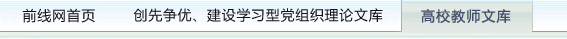|
| 再读库恩
|
| 作者:吴国盛 日期:2012-12-30 阅读:892 次
|
刊载于《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4期
摘要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摧毁了传统科学哲学的整个构架,使科学哲学学科进入反常时期。人们可以从库恩的思想中引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实践哲学,也可以引出科学解释学。怀着感恩之情重读库恩,作者发现反科学主义、第二种科学哲学、现象学科学哲学,均有其库恩来源。
关键词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科学解释学 反科学主义
Kuhn Revisited
WU Guosheng
Abstract: Kuhn's Structure destroyed the whol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ut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to anomaly period. One can develop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s as well as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from Kuhnian Philosophy.
Keyword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Hermeneutics of Science, Antiscientism
一
今年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后简称《结构》)出版50周年。这本大异其趣的科学哲学著作横空出世,搅得六、七十年代的英美科学哲学界“周天寒彻”。带着自科学史领域而来的质朴证据和闪光直觉,库恩的《结构》让科学哲学界无法回避但又难以下咽。70年代以来直至今日的科学哲学教科书,既无法回避库恩和“范式”,又无法纳入科学哲学的传统框架之中,只好将之置于边缘化的位置。由于库恩根本否定了传统科学哲学理解科学的基本路线,所提出的问题甚至让科学哲学整个学科遭遇灭顶之灾。费耶阿本德所谓“科学哲学,一个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根本就是库恩之后科学哲学的历史命运。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六神无主、苟延残喘的局面,都拜库恩所赐。正是由于《结构》对正统科学哲学的摧毁性,该书出版之后,一方面是好评如潮,另一方面则是恶评如潮。恶评来自科学哲学界,好评则来自四面八方。一位英国哲学家称库恩“充斥着荒谬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几乎没有几个现代哲学家会把他当回事儿。”[霍根 1997,页82]李创同教授认为,1961-1974年间,库恩共遭受了七波有时近乎“围剿”式的批评,批评者包括波普、夏皮尔、萨普、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戴维森、基切尔、普特南等,批评的目标指向他的“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甚至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李创同 2006,页213-220]扣在库恩头上的帽子主要是: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20世纪80年代,急风骤雨的批评声浪逐渐平息,库恩不再处在风口浪尖。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已经不再风头十足,而所谓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经过20多年的磨练,也已经成长壮大起来。1982年,美国科学史学会授予60岁的库恩“萨顿奖章”,这是国际科学史界的最高荣誉。1988年,美国科学哲学协会选举库恩担任主席。纪树立先生所谓“中年辉煌、晚年落寞、身后寂寞”[纪树立 1997],恐怕并不准确。中国学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可能与库恩在中国的遭遇有关。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80年代,“科学革命家”库恩才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但是从一开始,库恩就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喜欢。1980年,李宝恒、纪树立合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1年12月,以“库恩的科学哲学”为主题的第2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此前1个月,纪树立、范岱年等集体翻译的《必要的张力》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重要著作的汉译本的迅速问世,使中国学术界很快熟悉了库恩。80年代,也是中国科学哲学界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科学哲学的最新成果,令中国学人耳目一新,使科学哲学界几乎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哨阵地。“改革”者呼唤着的首先是思想“革命”、观念“革命”,而科学革命家库恩的到来正当其时。于是乎,“科学革命”、“范式”、“不可通约性”等概念词汇风行一时。
一种新理论之为革命性理论的,取决于受众对于传统旧理论的持守程度。如果你并没有坚信不疑因而需要坚守的旧传统,那么对你来说,一个新理论的出现也就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库恩对于中国学术界的情况恰恰就是这样。库恩在英美哲学界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英美哲学界有一个强大而顽固的分析哲学传统,有逻辑经验主义学派超过半世纪的“常规”发展所形成的丰厚“范式”,而库恩挑战了这个范式。反过来,中国学界并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这个深厚的背景,因此库恩对于中国学者整体而言,只不过是打开国门后涌进来的种种前所未闻的新奇理论之一,并无格外的特殊性和动人之处。进入90年代,中国学术整体滑坡,学术出版更是困难重重。曾经是国外科学哲学译介主力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杂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于1990年永久性停刊。纪树立教授作为80年代翻译波普和库恩的重要学者,在编译了《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之后,一直计划编译一本库恩的科学哲学选集,但直到库恩去世,这一选集也未能编成出版。自1981年之后,库恩的著作再无中译本面世。90年代前半叶的这一学术凄凉局面,一定影响了纪先生对于库恩晚年处境的判断。
90年代后期、新世纪初年,中国科学哲学界重新燃起对库恩的兴趣。库恩著作的翻译有重要的进展。在我主编的《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列入了库恩的4本著作:金吾伦、胡新和合作新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2003),吴国盛、张东林、李立合作翻译的《哥白尼革命》(2003),范岱年重新校订的《必要的张力》(2004)以及邱慧翻译的《结构之后的路》(2012)。还差一本《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库恩的著作就一网打尽了。令人惊喜的研究性著作要数2006年出版的李创同的《论库恩沉浮——兼论悟与不可通约性》。这部30多万字的著作,是作者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目前能够见到的华人学者对库恩最详尽最富有东方特色的研究。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哲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库恩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引导和启发意义,从库恩出发,走向科学知识社会学,走向科学实践哲学,走向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科学哲学。
80年代,作为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我早就读过库恩的《结构》和《必要的张力》。此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亦多次研读。这次为了纪念《结构》出版50周年,我重读这本自以为非常熟悉的20世纪哲学经典,越读越有深深地感激之情涌上心头:原来库恩的思想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从大的方面讲,库恩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相结合,以科学史的案例研究为基础来理解科学、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正是我本人始终遵循的研究路线。不止如此。回首过去20多年的历史,我所倡导的“反科学主义”、“第二种科学哲学”、“走向现象学科学哲学”,似乎都可以从库恩这里找到根据。本文略述一二,以志纪念和感恩之意。
二
中国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科学哲学界中的表现,是用新的自然科学来否定陈旧而教条的官方哲学。比如我自己也加入其中的,用现代宇宙学来质疑宇宙无限论,用粒子物理学来质疑物质无限可分论,用杰出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来挑战哲学指导论。这种富有批判精神的科学主义,在当时无疑有其现实意义。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些工作的局限性。在1993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自然本体论之误》(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序言中,我明确提出,主张哲学应向科学学习、主张用科学改造哲学,这些都只是拨乱反正,是纠正从前对自然科学的不公正,但仍然是一种政治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哲学的自主性,就像捍卫科学的自主性那样。哲学做哲学的事情,科学做科学的事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哲学无须追随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书中标榜自己是“反科学主义”的。不再追随自然科学之后,哲学应该如何做?书中开出的方子是:“追随历史”。为什么不是像当时主流的科学哲学家那样“追随逻辑”呢?一方面是柯林武德的影响(我在80年代后期翻译过他的《自然的观念》),另一方面看来是库恩的影响。
库恩用以颠覆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就是科学史,但却不是通常的科学史。通常的科学史,或者说许多理科教师和学生眼中的科学史,都是不同形式的大事年表,是按照今天科学的范围和对错标准来选择历史材料,最后以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的历史故事。这种科学史也的确是科学史学科早期流行的科学编史模式,已经被称为实证主义编史学、辉格史。我则愿意称之为“科学家的科学史”,以与“(职业)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相区别。《结构》第一章“历史的作用”开篇就指出,历史确实可以帮助形成一个崭新的科学形象,但不能是老一套的历史。老一套的历史跟理科教科书一起,共同构造了一个歪曲的科学形象。库恩的目标,准确地说,不是用科学史来改造科学哲学,而是同时推出新的科学史和新的科学哲学。库恩明确表示,柯瓦雷是这种新科学史的代表人物,而他本人试图使这种新的编史学更加落到实处。
旧的科学形象和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一个事实积累的逐渐进步的过程,是越来越逼近真理的过程。这样的科学观并不只是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独撰生造的,而是科学共同体对科学事业的自我理解。这是库恩思想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他把旧的科学观说成是科学家的自我理解,并没有责怪科学家的意思,而是把这种现象解释成常规科学的必然结果。在以“革命是无形的”为题的《结构》第11章,库恩仔细分析了为什么科学家往往只感觉到了知识的进步而没有感觉到革命的存在。他认为,这与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的方式有关。科学家和普通人的科学观都是由教科书、普及读物和科学哲学著作这三类书籍塑造而成的,而这三者都“系统地隐瞒了科学革命的存在和意义”。这三类书籍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教科书,普及读物和科学哲学著作只是对教科书的通俗化或形式化。“部分由于选择,部分由于歪曲,早期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所遵守的规则,都被刻画成与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的产物完全相同。无怪乎在每一次科学革命之后,教科书以及它们所蕴涵的历史传统都必须重写。也无怪乎随着它们被重写,科学再一次看上去大体像是个累积性事业。”[库恩2003,页124-125]教科书作为科学教育的主要工具,培养和制造了辉格式的科学史,从而使得科学事业像是积累性的。受教科书影响的科学家,也是这样回顾自己的研究历史的。
库恩岂不是在说,科学家对他们自己从事的事业其实并不理解,而且充满误解?他就是这个意思。库恩的这个说法,在中国当前的学术环境下,或许会被说成是“反科学”,说成是大逆不道。可是,库恩在英美学术界所受的责难主要来自哲学界而不是科学界,说明那里的科学界并不在乎哲学家说三道四。实际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就是人类事务的常态。库恩只是指出科学也不例外而已。
三
作为反科学主义思想的一个学术延伸,我在1996年提出“第二种科学哲学”的概念,也就是在英美传统的实证主义、逻辑主义科学哲学之外,发展以批判科学、揭示科学的可能性条件及限度为主旨的科学哲学。第二种科学哲学的主要思想资源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因此,近些年我一直在与同行们尝试开辟“现象学科学哲学”(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新道路。现象学科学哲学之所谓“批判科学”,并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像康德那样反思科学、揭示科学的先验条件和限度。美国现象学家柯克尔曼说得好:“的确,现象学从一开始便反对对科学持一种单面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解释。然而,现象学所反对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之中蕴涵的自我哲学理解。因此,现象学所反对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不是经验研究及其成就,而是对科学的实证主义解释。”[Kockelmans 1993, pp.124-125]
现象学科学哲学是一个多样化的家族,其中最重要最成熟的一支是科学解释学,而库恩应该看成是科学解释学的开山鼻祖。德国的解释学传统经历了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文本解读方法论,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生存情境本体论的演变,但是,均没有把自然科学纳入解释学。对狄尔泰而言,解释学是区别于自然科学方法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对伽达默尔而言,虽然解释学已经面向一切人类活动,但优先的适合领域仍然是艺术经验和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库恩在《结构》中从未提及解释学,而且当时的他似乎也并不了解德国解释学传统以及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库恩的科学解释学完全独立地从自己独特的科学史研究中产生出来,直到在1977年出版《必要的张力》一书时,他才在序言里明确把自己的工作标定为解释学。但是,生活在美国哲学环境下的库恩,此后并没有致力于扩展这一“解释学转向”(Hermeneutic turn),而是长期置身于分析哲学的漩涡之中自我申辩、防御退却、起起落落。完成被库恩本人搁置起来的“解释学转向”,仍然是当代另类科学哲学(或我所谓第二种科学哲学)的重大任务。
库恩的科学解释学起源于对科学文本的释读经验。1947年,还在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库恩受校长柯南特的委托,参与讲授一门改革试验的科学史课程。为了备课,库恩去阅读当时的主要科学文献。他发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的文献非常好懂,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则显得莫名其妙,甚至是胡言乱语。他在思考,为什么一个在政治学、生物学、艺术批评领域如此睿智和超群绝伦的人,在物理学领域却显得如此浅薄、如此幼稚?为什么这样错得离谱的物理学理论却长时间受到尊重和认真看待?终于,他突然意识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主题与近代物理学完全不同,这是导致从今日之眼光看来它完全荒谬的根本原因。一旦回到他自己的主题范围中,他就立即拥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和理路。
这年夏天的困惑和顿悟,使库恩开始发展一种新的对待古典文献的阅读和理解方式,并构建自己的历史叙述模式和叙述理论。他提出一条对待历史的原则:“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显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了一种答案,我还要说:有些段落虽然讲得通了,但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为懂了,现在意思却全变了。”[库恩2004,序言]如何才能真正理解那些表面看来荒谬的著作呢?库恩说,“对过时的文本恢复过时的读法”[库恩2004,序言]。
如果说库恩的这种释读经验还只是让“科学史”回归“历史”学科固有的解释学方法论之中,那么《结构》中提出的“科学革命”理论、“范式”和“常规科学”概念,则是把“自然科学”纳入普遍的解释学之中,揭示出自然科学这种向来被认为是特殊的人类活动样式,同样遵循解释学的普遍原则。
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家寻找中立而客观的科学事实,以逻辑和理性的方式建构理论,从而获得客观而有效的真知识。科学家是这样工作的吗?当然不是。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库恩都始终强调科学家之所以是科学家,就在于他们始终在范式之下工作。没有范式,科学研究无从下手,只能陷入像人文学科那样的总是从头开始、众说纷纭的局面;没有范式,就没有科学特有的积累性进步。常规科学是科学的常态。一个人唯有处在常规科学之中,从事常规科学工作,才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由一个逻辑问题(可证实或可证伪)变成了一个社会学问题:你处在科学共同体之中,你就是科学家,你做的事情就是科学,否则就是非科学。库恩对常规科学的重视,展现了他作为“科学革命家”的保守的一面。收敛和发散之间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的观点,体现了库恩哲学的深邃之处。
为什么需要范式呢?范式规定研究的问题域。对于一个好奇求知的心灵来说,宇宙之间充满了无穷的未知之处。如果随机和偶然地抓住一个问题进行研究,那多半不能获得成功;如果一群人都如此,就不会有历史上取得巨大进步的科学事业。像弗兰西斯•培根所主张的那样,组织一大群研究者对宇宙间的事实进行搜集、归纳和整理,从而得出一般规律,根本没有可行性。近代科学也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范式的引导下,那些有意义的事实和问题浮现出来,供科学家去发现、检验、精确化。在哥白尼天文学的范式下,去发现恒星周年视差是有意义的,而在托勒密范式中,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在范式中,有些问题注定是有解的,因而值得为“求解”去耗费精力。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就是“解谜题”(puzzle solving)。只因为有范式,才有“谜底”。科学家们从事研究工作时,肯定要相信“谜底”的存在,而且对猜谜规则深信不疑,否则就不会有解谜活动。范式同时规定了问题域、问题的解法、评价解法之优劣的标准、问题可能的答案,也规定了反常之为反常。超出这个范围的事实、问题和答案,或者不会向常规科学家显示,或者偶尔显示出来也不会引起常规科学家的关注,或者引起了常规科学家的关注也不知如何处理。第谷之前的西方天文学家,不会有新星、超新星的记录,因为天空不生不灭的教条制约着他们。强调前见、教条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是库恩科学解释学的第一发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发现的“观察渗透理论”(theory-laden)也属于这种理论解释学。
除了理论解释学之外,库恩更为重要的是为实践解释学打开了缺口、铺平了道路。在《结构》的第5章“范式的优先性”中,库恩提出了范式并不等同于而是优先于一组“合理性规则”,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整套规则的存在。范式存在于教科书、课堂讲演、实验室的实验中,对常规科学家起示范作用,因此,范式的主要功能是让科学家“有事干”、“懂得如何干”。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范式作为范式就不一定要合理化、形式化、规则化。并且库恩相信,范式起作用的许多方式中,多数根本没有可能理论化、条理化、逻辑化。正因为如此,科学革命前后的两种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因为如果两种范式都能够被形式化,那么范式转换就可以诉诸逻辑检验。库恩反复强调范式的实践特征,强调如果没有实际操作演练活动的话,理论单独不可能发挥作用。相反,即使范式中的诸多理论尚未达成逻辑一致性,也不影响范式指导科学研究。因此,范式比共有规则更具优先地位。这里,不仅支持了波兰尼“意会知识”的理论,而且提出了一种实践优位(practice-dominance)的科学哲学。
《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出版50周年了,它的影响和地位跟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颇有相似之处。它们的书名都讲Revolution,它们的观点都惊世赅俗,它们的作者都有点保守、有点胆怯。更相似的也许是,哥白尼革命只是由哥白尼发起而非由他完成。完成哥白尼革命的是半个多世纪后的开普勒。库恩也只是提出了问题,摧毁了旧的范式,而新范式进入常规还有待时日。我们仍然处在科学哲学的反常时期。
参考文献
霍根 1997.《科学的终结》. 孙雍君译.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李创同 2006.《论库恩沉浮》.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纪树立 1997. 了却一桩心事. 《读书》第1期.
Kockelmans, J. J. 1993. Ideas for a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库恩 2003.《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库恩2004.《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纪树立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