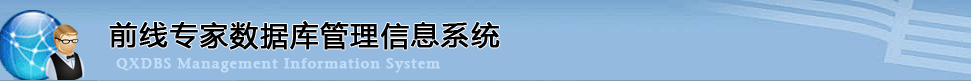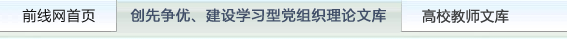| 构建以新政治观为核心的中国话语体系 |
| 作者:公方彬 日期:2013-05-03 阅读:4431 次 |
|
摘要 中国与西方国家、甚至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话语系统存在差异。如果从走向世界或追求民族崛起的高度谈中国话语系统,就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模式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要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话语系统,必须要以世界的眼光和胸怀看问题,必须要加强创新能力,这决定着新的话语系统的构建时间与质量。 关键词 话语体系 制度差异 心态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首先需要明确建设目标与坐标系。如果以既有的话语系统为坐标,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类似的工作,所做的仅仅是改善和调适。如果站到中国走向世界或追求民族崛起的高度谈话语系统,就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模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广且深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 以世界为坐标,中国与西方国家、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话语系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政治和文化紧密联系。事实上,话语系统原本就形成于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中。我国的话语系统有两大基因:一个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文化,另一个是革命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二者都带有根本性、特殊性,因而将我们与西方世界的话语系统区别开来。笔者主持过一个25国军官探讨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研讨活动,深切感受到这种差异。我们的军官谈军人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围绕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展开,突出的是我军的政治属性,并且语言模式基本一致,其他国家的军官主要是围绕军队的国家属性展开,特别突出军队的文化属性和军人的职业属性,语言风格也各不相同。与此类似,在南通召开的“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上,有25个国家的近60个城市的市长或市长代表与会,有记者旁听或采访后感慨,大多数中国市长们的发言水平与其他国家(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市长有明显的差距或者区别,中国的市长发言不讲场合,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话语系统。” 如果话语系统仅仅是表达方式,那么在一个多元并且强调包容的时代,各个国家尽可保持自我。如果是一个小的国家和民族,同样不必在意语言差异而来的摩擦和碰撞,有时候小国恰恰需要以此体现存在。问题是,话语系统背后折射的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正在由跟着别人的鼓点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如果不在意差异、不减少差别寻求共同点,只能导致越来越多的摩擦和冲撞。比如,围绕疆独分子热比娅,我们与西方国家打了许多口水仗,几乎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似乎相互听不懂对方的话语。在语言沟通困难的背后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我们认为,你尊重我的主权,就不能接纳热比娅,同时要管住你的下级政府和官员。他们认为,由于政党轮替、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总统不能也无权干预个别议员或州长市长的行为。像这样的差异,如果无法找到突破口,冲撞难以避免。 理论上讲,冷战结束后我们已经在党章中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即不再输出革命,同时西方开始强调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的理论,这也说明政治制度已经不是其国家对抗的最重要的考量指标。既然如此,冲突为什么不减反增呢?虽然传统的政治制度博弈弱化,但新的利益冲突、文化或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更加凸显。中国要崛起,美国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必然要对中国遏制包围,这便成为新的冲突根源。包括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带有必然性,因为中国要崛起,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的运行秩序,这需要适应,需要实现新的平衡。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尽管客观原因难以避免,但侧重主观上认识矛盾和问题,实为积极和主动。因为,改善规则首先要适应规则,抑或改变世界首先应融入世界。
构建以新政治观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 只有确立新政治观,才能避免以革命斗争理论来推进和谐世界建设。当今世界,政治、利益、核心价值观三大博弈的消长,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话语系统。国家利益博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国家间的交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当前,国家利益博弈基本没有变化,但政治制度与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出现了消长。其中,政治制度博弈在弱化。这不是缘于“阶级斗争熄灭论”,而是源于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已经没有几个,政治力量失衡使国家集团形式的对抗不复存在,主战场消失,零星对抗不足以构成国家博弈的主要形式。比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拥有相当的力量,但在西方许多人的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再加上我们的党章已经删除国际共运的内容,并且明确昭告世界,我们不再输出革命而求世界和谐。与此同时,核心价值观的博弈愈来愈突出。因为,既然意识形态对抗走向终结,必然有新的力量来填补真空,于是“文明的冲突”的理论产生出来,文明冲突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冲突,而文化的内核便是核心价值观。 阶级斗争的理论开始被摒弃,新的与时代相联系的价值系统亟待建立,但由于思维惯性,很多人的思想仍然处在二元对峙的阶段,并有加深加重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反映在对意识形态斗争现状与发展走向的判断。当然,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实践。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们批评西方国家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并且将体育问题政治化,同时我们又一再强调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办好奥运会。又如,不久前中央媒体强调楼市调控是政治问题,来不得半点动摇。将民生问题政治化是我们的惯常做法,也是我们话语系统的一大特征。这在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并无不妥,但若走向世界,就会产生脱节和错位之感。所以,不跳出以政治制度为标准的思维窠臼,难免出现国家交往上的尴尬。一方面强调“好同志、好兄弟、好邻居”,另一方面利益冲突几近兵戎相见。来自西方的表扬我们乐意接受,若是批评则必从遏制和打压的角度理解,哪怕是善意的批评。政治制度的对抗带有根本性和不可调和性,仅仅以政治标准而不是伦理标准、法理标准,必然会从对立的立场上认识和处理问题,对此可佐证的事例很多。今年初,美国发布人权白皮书,内容中涉及对大陆和台湾的批评,我们的反应一如从前,认定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于是进行了还击,而台湾方面则强调对美国指出的问题进行反省和改善。或者这样说,不能跳出以政治制度为标准评价世界,很难避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对峙价值观。笔者访问过加拿大,其军队仅6万人,其中8000人在国外执行任务或准备到国外执行任务,他们直言这是为了获得世界领导权。美国曾邀请我们出兵阿富汗,受制于传统理念我们没有出兵,结果只能动口不动手,利益攸关方的责任无法履行,世界影响力更难产生。当然,被孤立的现状也很难改变。目前世界上强国弱国都结盟,欧盟、阿盟、非盟、东盟等等,中国坚持不结盟,这就是传统政治观决定的。所以,不能确立新政治观,国家利益在受到损害时很难有效维护,因为维护自身利益就很难不触碰“不干涉内政”的政治理念。 只有找到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才能改变以“阶级仇民族恨”为支撑的精神大厦。在精神力量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产生途径。西方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其精神力量来自三个方面:政治、宗教、职业精神,其中宗教信仰是其精神大厦的根本支撑。我们主要是通过政治信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与阶级斗争的对抗性,决定了“阶级仇民族恨”是我们的精神激励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式。直到今天,仇恨教育仍然是我们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比如,传统教育中涉及回顾历史以关照世界并确立价值坐标,一定离不开中俄瑷辉条约、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等。可以说,在找到精神力量新的产生途径前,不管世界政治生态如何变化,逝去的历史多么久远,不管多么强调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我们的价值系统都不可能离开对抗性思维及仇恨教育。 存在即合理,有这样的传统亦无不可,问题在于世界和社会的变化已经不能支撑传统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比如讲爱国,我们习惯以爱国的尺度评价体育活动,往往一个拳师比武也要上升到爱国的高度,问题是今天我们已经走出国门引进球员,如用传统标准评价,我们引进的是一些不爱国的人,以不爱国的人来调动民众的爱国热情不合逻辑。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在双重国籍已经进入立法视野的今天,若不能重新诠释并廓清爱国主义,理论和实践就会脱节。那么跳出阶级对抗的方式又会怎样呢?至少目前尚无法避免精神世界的虚无。道理很简单,我们是一个缺少宗教信仰的民族,工业革命迟迟没能关照中国,寄望于改革开放后30多年完成职业精神的塑造是不现实的。既然调节精神世界的不外政治、宗教和职业精神,那么我们所能够作出的选择只能是“阶级仇民族恨”。以这样的价值坐标面对世界,矛盾和冲突很难避免。笔者访问加拿大期间曾提出两个问题,对英法殖民史、朝鲜战场上中加军队刀枪相向怎么看?对方回答很轻松:“那就是个历史事件!”可见,两种历史观和不同的精神力量激发途径放到一起,必难沟通。
提升价值追求是话语体系的重中之重 只有提升价值追求,才能把握大国兴起的本质,避免以利益为评价尺度,以金援谋求话语权。当今世界,中国要赢得话语权必须弄清一个问题:我们除了谈利益、开支票,还能不能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拿得出,那么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次要的,稍作调整他人即能听懂且愿意听;如果拿不出,就会出现去年东盟论坛上的尴尬:“一个无比孤独的中国,处在闹市之中,看上去像个阔佬,大把撒钱给邻居,希望获得友谊,而邻居们并不领情,一边将钞票快速塞进怀里,一边转过头去与美国含情脉脉。”出现这样的尴尬,究竟是别人不领情,还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再以中非论坛为例,自开坛以来,我们无比慷慨地送出一个个大礼包,这是否是最佳选择也需要研究。至少以一国对一个国家集团,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想当头,而当头的国家只有掏钱的份。尤其是一个人均国民收入排在百名左右的国家,大把掏钱援助一些人均收入超过我们的国家,看上去很美,但给人怪怪的感觉。为什么中国现在援助贫穷国家,也援助发达国家,掏出的是真金白银,收获的却是“中国威胁”、“经济侵略”?个中原因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当今世界,仅仅有钱是不够的,海湾国家的富有让世界羡慕,但没有人敬佩。可以说,如果整个价值体系和话语系统仅仅处在利益层面,是很难真正服人的。 我们的价值观与世界主流价值观存在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以目前发生争执的内容为例,西方提出人权超越主权,我们强调不干涉他国内政;西方人讲自由表达和民主选举权,我们讲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两种价值观没有对错,但需要我们充分认识的是,在人类文明进入全球化时代,独立话语系统越来越受主流话语系统考验的情况下,价值观不能与人类文明同步必被排斥。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人们其实对豪华并不敏感,更敏感的还是文化,每每都为灿烂的文化、创新的文明而骄傲、而感动。为什么希腊队每次都是第一个入场?既不是国家富有,也不是体育强国,而是在人类发展史上他们创造了惟一一份让世界息战而走到一起的历史遗产。中国的传统文化柔而非刚,驰而非张,中原文明历来缺少扩张能力,既然这样,本不应当让世界产生威胁感,原因之一是百年屈辱后极想强大起来的我们,太想让人知道我们已经强大,有了这样的心理,即使嘴上谦虚,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张力。比如北京奥运会我们搞圣火境外传递,但历届奥运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大规模搞境外传递。更值得思考的是,近年来我们开展的大规模外援,为什么别人不是从中解读出责任和担当,而是指责我们以经济力量征服别人。大概这也是一位与中国友好的政治家一再提醒中国要学会谦虚的原因所在。我们经常批评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径,解读其打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皆因石油而来,这种批评也是双刃剑。只讲利益而不谈道义和文明冲突,不仅无法让我们赢得话语权,甚至加重了中国经济威胁的口实,也就是说既然中国解读国家行为全在利益,那么中国强大后也一定以自身利益为坐标,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大国应有的道义责任。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都带着经济目的,但较少谈利益,更多的是谈民主自由人权?就是为了占领道义的制高点。 只有跳出以美国为主轴的外交路线,才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支撑新话语系统的外交理念。有外电评论,中国目前的外交是以美国为主轴,对其他国家关系则以亲美反美决定亲疏。这一判断未必准确,但却引发我们思考中国的外交奠基于何种价值坐标之上的问题。中国外交曾经形成过独立的价值坐标和运行方式,这就是美苏争霸之时,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联合第三世界与两个超级大国抗衡,那时目标和方式清晰明确。苏联解体后美国独霸世界,中国的制衡作用丧失,虽然尚不具有与美国直接对抗的能力,但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又无法与第三世界国家相提并论,于是第三世界虽不能说与我们渐行渐远,至少很难再划入一个阵营,这也是中国大力援助非洲国家,赢得的却并不是都是感激,尤其不再以兄弟相待的重要原因。此时,中国既不是领袖国家,又不再是需要抱团取暖的弱小国家,形象开始变得模糊,由此引来世界大报的评论:“世界激辩中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既然世界已经无法认清中国的性质,那么也便反证着我们没有清晰的价值坐标和评价尺度,外交进入跟着感觉走、跟着利益走、跟着短期目标走的怪圈。 跟着走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跟着走。国家是这样,人也是这样。有领头者,有追随者,惟此才形成秩序。只不过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国领得不那么好,与此同时经过百年屈辱的中国人又太想享受“山高我为峰”、“会当凌绝顶”的感觉。这就决定了要形成有中国参与的新秩序,就必须提出风格鲜明的国际理念、架构和规则。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已经由跟着别人制订的规则跳舞到世界开始谈论北京共识,这就决定“藏拙”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现状。比如我国国防部长访美时讲到一个观点:中国军力比美国要落后20年,我们没有力量挑战美国。这原本是想释放善意,美国人却说,不在于中国能不能挑战美国,而在于中国为什么要挑战美国。西方人要求我们公开自己的目标和企图,我们也有必要确立一个清晰的与人类文明走向一致的独立价值坐标,以指引自己的外交。如不久前安理会关于涉叙方案,我们反对就必须讲清反对理由,同时提出优于原方案的新思路,否则就可能被视作搅局者。不再推动国际共运,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方式便不存在,政治制度差异构成的敌友关系也不存在,可供选择的便是利益和核心价值观,又因为利益为主轴的外交方式不会支持大国崛起,至少无法获得道义力量,那么可供选择的只能是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一定意义上,我们能不能产生影响世界的话语系统,直接取决于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中国要摆脱以美国为主轴的外交战略,很重要的是对自己当前的力量与今后较长时间内的力量增长有一个客观准确的判断,如果距离当领导者很远,仅凭愿望而挑战美国,带来的只能是围堵,是更多的敌人。总之,在形成话语系统的过程中,我们的历史方位要清楚,现状和发展目标要清楚,与美国和各个国家集团的关系要清楚,以国家利益或核心价值观为主轴的外交理念要清楚。有了这些,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便自然形成。
包容不同制度和文化是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 只有认清不同制度和文化并给予理解和宽容,才能避免因差异和误读而来的冲撞。当年胡耀邦同志到五台山游览,在释迦牟尼塑像前拜了一拜,同行的人很惊讶,共产党的总书记怎么会拜佛呢?胡耀邦说了一句话:“你我信仰不同,互相尊重。”这一点放到当前中国确立新话语系统过程中,也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因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是根本差异,如果无法做到“互相尊重”,便不能求同存异,无法实现和谐。比如,一方面大量借鉴西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领域的优秀成果,而另一方面又大批西方政治制度的腐朽,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再者,一方面揭露西方社会的丑陋,一方面又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留学,甚至将家属移民西方国家自己当“裸官”,无论如何都不具有说服力。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尊重各自的选择,关键是阐述好一个道理:“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西方再好我们也不可能把十几亿人都移民出去,最根本的,还是在这块土地上自我拯救。 中国与西方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是权力运行。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西方政府权力相对有限,中国政府权力相对无限。这就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比如,中国政府访问团到美国访问,更愿意搞政府间的对等谈判,而不愿意到其国会、基金会、智囊团演讲,以阐明自己的理念。我们往往认为摆平了美国政府就摆平了美国,其实,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下,政府权力有限,摆平了美国政府远不能摆平美国。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境外传递至英国伦敦,藏独分子沿途挂起雪山狮子旗,我们要求其政府出面制止,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国家很容易解决,因而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分,但在他们政府那里绝难办到,因为权力制衡与法律规定都不允许其政府出面制止,除非藏独分子违法。至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同样影响着价值判断和行为,比如国家统一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各民族生活于一个大家庭,合得来就相处,合不来就分家,不必强求,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搞一次公投就可以分解国家,这对于长期受大一统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也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西方强调个体和个性,西方的主流产生于每一支流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是主流改变支流的结果,西方不同人都可以发声,并且只代表自己,我们强调一个声音说话,因而把西方议员的作秀看作是官方立场,这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再比如,西方政治理论把政党和政治家作了偏负面解读,再加上媒体的独立和天生监督政府职能,因而政党和政治家一直在被骂中前进,我们把政党和政治家与精神系统相联系,认为骂多了会削弱精神力量,因此不允许骂,这就出现了我们天天骂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并不太在意,而西方一个政客的批评我们便受不了,甚至媒体人的抓眼球性批评也会惊动我国外交部。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认真把握,说不到一块去是必然的,更遑论深入沟通。 只有克服弱国心态、确立大国胸怀,才能站在世界看世界而不是关在门内看世界。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要想当老大,就要学美国脸皮厚。他的意思就是当头注定挨骂,如果没有包容度也就不要当领袖。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讲,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加上儒家的皇权与等级制度,造就了人格上的不平等,因此中国不缺老爷,也不缺奴才,但缺少平等意识基础上的公民。这就形成了特有的价值观,要么臣服于人,要么让人臣服,很难做到与人平等相处。与此同时,基于百年屈辱的历史与文化上西强我弱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弱国心态和防范心理,由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上的三级跳,由被援助到援助别人,由援助第三世界到援助不久前还援助我们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必然让那些心理不成熟的人产生膨胀心理。不平等的价值观念与防范心理、膨胀心理结合起来,也就导致即使走出去看到了世界,仍然无法客观认识和把握世界,就如当年一位文学家访问美国,她从纽约摩天大楼阴影中看到一个流浪汉,由此推论资本主义走向腐朽。所以,依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以世界的眼光和胸怀看问题极其重要,这甚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话语系统的形成。 综上所述,要建立与世界接轨的话语系统,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力气加强研究,一定意义上,思想有多解放,创新能力有多强,就能获得多大的突破,且决定着在多长时间内形成我们新的话语系统。对于解放思想和提高创新能力是很长时间以来中央突出强调的。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实际上,理论创新、尤其政治思想领域的创新是最困难的创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很多人更习惯于守旧,而不善于创新,凡有创造性观点产生出来,不是看其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看领导人有没有讲过,这样的结果导致了我们的理论严重滞后,无法解读自己的实践创造。在话语系统建构方面,真正要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必须站到邓小平讲的“人类共有的文明”,江泽民讲的“政治文明”的层面或角度来认识问题,形成新的政治观和政治坐标,同时明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西方听得懂,真正富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系统才能产生出来。 Building a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with New Political Concepts as Its Core Gong Fangbin Abstract: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differs from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 or even the majority of world countries. If talking about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joining the world or pursuing China's rise, it is not only an issue of language model, but a mor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je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discourse system conforming to world standards, we must look at various problems with a worldwide view and mindset and strengthen innovation abilities, which determines the time needed to establish the new discourse system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it. Keywords: Discourse system,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mindset 【作者简介】 公方彬,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研究方向:军队思想建设、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等。 主要著作:《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政治作战初探》等。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