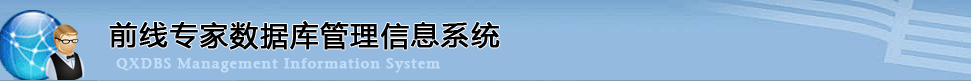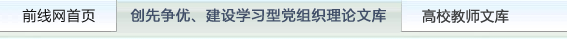| 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 |
| 作者:公方彬 日期:2013-05-03 阅读:4402 次 |
|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现阶段最重要的执政理论,要将其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由重点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向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延伸,即由经济基础上升到上层建筑。怎样才能实现这一重大转变?取决于政治观的发展程度,或者说能否顺应时代,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这已经是个绕不开的命题。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在几近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步履维艰,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或决策层的决心与勇气,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理论支撑不够,也就是政治二字横亘在面前。笔者认为,在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与诠释前,即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囿于表层,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讲政治要与时俱进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治必须顺应时代,不断调整自己。就世界来讲,伴随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不再“输出革命”,同时认定中国社会的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再加上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两大建设目标,我们便有理由认定今天的政治观已经大大区别于昨天的政治观。如此,不能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和诠释,就无法顺应和吻合时代,就会出现屁股坐在现代政治上,脑袋却囿于传统政治中,进而也便不可能确立现代政治坐标,没有新政治观的形成,价值坐标也无法确立,模糊必导致内政外交陷入窘境。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更无法总结和抽象出“中国模式”。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清自己,便无法切割与僵化社会主义的差异、与现存的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更不能切割与西亚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而无法做到正确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讲不清制度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优于别人的政治观、核心价值,结果只能以利益关系和开支票来赢得话语权,而钱买来的国家关系和支持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还可能模糊自己的形象。为什么我们支持利比亚、叙利亚等过程中承受了那么多的质疑?为什么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冲撞越来越广泛而持久?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面对社会,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会出现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是不合拍的。这其间的逻辑关系不难理解,但实践中我们似乎更习惯于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推进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其他各领域的工作,至少尚未借助法理、伦理和宗教推进政治。诚然,在革命战争年代,甚至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的力量都是强大无比,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问题是冷战结束与党的执政理念的变化,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已经不支持过去那种政治,及其那种政治中生发的力量。这一点从冷战结束我们社会受到的精神冲击要远大于西方可以看出。西方社会之所以在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过程中未受太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其精神力量并不是通过政治运行获得,而是从宗教中形成。本质上讲,西方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差异很大,西方政党轮替一般不会讨论政治制度问题,即不是政治路线上的差异,仅仅是执政理念的较量。华盛顿甚至说美国不需要政党,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实没有政党,不久前奥巴马还说,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就不同了,不仅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就是一些政治思潮也时时影响着人们。作为讲政治的社会,政党及其政治理念影响带有根本性,这也是我们国家性政治活动都一再强调讲政治,我们党的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都一定要讲旗帜、理论、道路和制度这些重大命题的原因。问题是世界政治走到今天,党也开始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原有的政治系统和精神建构方式已经无法直接观照现实。笔者出访加拿大,导游是一位移民的共产党员,他调侃说自己潜伏在加拿大,什么时间解放军打过去的时候,他会号召其他的潜伏者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灭掉。这是否可以引出一个重大命题,热战到冷战可以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支持政治信仰,当《党章》中删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后,支撑信仰的终极和永恒在哪里?这就说明,如果不发展和重新界定政治,就无法解决人们目前面临的大量困惑,精神力量也便无法找到新的生长点。 党承担了太多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走过许多弯路,有过很多教训,但值得骄傲的东西更多,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清末民初上百个政党都宣称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情况下,最后中国共产党胜出,且带领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在十年“文革”经济濒于崩溃的基础上实现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这样,我们却能感受到,党和政府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自然有民众心态和价值观变化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由感恩心理向纳税人的心态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党和政府做得好属应该,做不好多受指责。换句话说,做好100件事中的99件是责任,一件做不好是失误,必然也必须受批评,这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特点。 正是这一特点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必须审视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权力集中对执政意味着什么。诚然,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定权力集中使党获得了强大力量,因此做了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事,但随着社会的开放,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散与多元,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趋向多元,这时试图以一元替代多元,以一元满足多元,几无可能。因为,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是无法以物质利益解读的。所以,是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无度的欲望。这就决定着我们必须考虑掌握多大权力和掌握什么权力的问题,涉及到承担什么责任和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政党和政府远没有承担我们党和政府这样沉重的压力。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与洛克等人的政治理论建构起来的政治体制,概括起来讲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权力有限,按照权小责小、权大责大的原理,西方的民众对政党和政府没有过高的要求和期望。比如,人们经常讲在美国要见个州长、市长很容易,预约一下即可,门口也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而在中国不仅见省市领导难,就是见个县委书记也不容易。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改变了人民公仆的性质?显然不是,根本原因还是权力分配和权力运行决定的。在西方社会,如果精神出了问题进教堂,如果想赚钱进市场,如果发生法律纠纷就进法院,甚至许多公共事务也是由社会组织来完成。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下,党和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同时几乎承担了一切责任,所以就没有可能像西方那样处理官和民的关系,类似的问题不予以讲清,也便容易造成比较中对党和政府出现不认同。也就是说,一党执政,且有着无限承诺,永远执政,必无法卸责,那么就很难避免权大责大,期望高失望大。显然,这一点在革命状态下和执政状态下认识差异很大。革命状态时的政治斗争几乎一切围绕“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大大的”,这个过程甚至不太在意手段和方式。不仅这样,甚至权力集中的理念要表现到思想领域,也就是统一思维、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执政状态下利益和价值观出现多元,政党可以统一思想,社会却无法统一起思想来,充其量形成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现阶段最重要的执政理论,要将其上升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必须由重点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向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延伸,即由经济基础上升到上层建筑。怎样才能实现这一重大转变?取决于政治观的发展程度,或者说能否顺应时代,重新界定和诠释政治,这已经是个绕不开的命题。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在几近共识的情况下仍然步履维艰,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或决策层的决心与勇气,其实最大的问题是理论支撑不够,也就是政治二字横亘在面前。笔者认为,在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与诠释前,即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只能囿于表层,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讲政治要与时俱进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治必须顺应时代,不断调整自己。就世界来讲,伴随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冲突理论渐成主流,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不再“输出革命”,同时认定中国社会的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再加上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两大建设目标,我们便有理由认定今天的政治观已经大大区别于昨天的政治观。如此,不能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和诠释,就无法顺应和吻合时代,就会出现屁股坐在现代政治上,脑袋却囿于传统政治中,进而也便不可能确立现代政治坐标,没有新政治观的形成,价值坐标也无法确立,模糊必导致内政外交陷入窘境。 面对世界,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无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特色社会主义,也无法解释中国的制度优势及在其基础上创造的经济奇迹,更无法总结和抽象出“中国模式”。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清自己,便无法切割与僵化社会主义的差异、与现存的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更不能切割与西亚北非等国家所存在的制度差异,进而无法做到正确处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讲不清制度的本质,就无法产生优于别人的政治观、核心价值,结果只能以利益关系和开支票来赢得话语权,而钱买来的国家关系和支持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还可能模糊自己的形象。为什么我们支持利比亚、叙利亚等过程中承受了那么多的质疑?为什么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冲撞越来越广泛而持久?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面对社会,政治不能吻合时代变化,就会出现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相对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相对于依法治国的理念,显然是不合拍的。这其间的逻辑关系不难理解,但实践中我们似乎更习惯于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推进思想、文化、经济和社会其他各领域的工作,至少尚未借助法理、伦理和宗教推进政治。诚然,在革命战争年代,甚至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的力量都是强大无比,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问题是冷战结束与党的执政理念的变化,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已经不支持过去那种政治,及其那种政治中生发的力量。这一点从冷战结束我们社会受到的精神冲击要远大于西方可以看出。西方社会之所以在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过程中未受太大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其精神力量并不是通过政治运行获得,而是从宗教中形成。本质上讲,西方的政治与我们理解的政治差异很大,西方政党轮替一般不会讨论政治制度问题,即不是政治路线上的差异,仅仅是执政理念的较量。华盛顿甚至说美国不需要政党,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实没有政党,不久前奥巴马还说,美国没有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出了问题。我们就不同了,不仅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就是一些政治思潮也时时影响着人们。作为讲政治的社会,政党及其政治理念影响带有根本性,这也是我们国家性政治活动都一再强调讲政治,我们党的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都一定要讲旗帜、理论、道路和制度这些重大命题的原因。问题是世界政治走到今天,党也开始由革命党进入执政党,原有的政治系统和精神建构方式已经无法直接观照现实。笔者出访加拿大,导游是一位移民的共产党员,他调侃说自己潜伏在加拿大,什么时间解放军打过去的时候,他会号召其他的潜伏者与解放军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灭掉。这是否可以引出一个重大命题,热战到冷战可以通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支持政治信仰,当《党章》中删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和任务后,支撑信仰的终极和永恒在哪里?这就说明,如果不发展和重新界定政治,就无法解决人们目前面临的大量困惑,精神力量也便无法找到新的生长点。 党承担了太多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走过许多弯路,有过很多教训,但值得骄傲的东西更多,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清末民初上百个政党都宣称代表中华民族未来的情况下,最后中国共产党胜出,且带领人民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在十年“文革”经济濒于崩溃的基础上实现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这样,我们却能感受到,党和政府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自然有民众心态和价值观变化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由感恩心理向纳税人的心态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党和政府做得好属应该,做不好多受指责。换句话说,做好100件事中的99件是责任,一件做不好是失误,必然也必须受批评,这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特点。 正是这一特点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必须审视集中力量办大事和权力集中对执政意味着什么。诚然,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定权力集中使党获得了强大力量,因此做了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事,但随着社会的开放,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散与多元,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趋向多元,这时试图以一元替代多元,以一元满足多元,几无可能。因为,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都是无法以物质利益解读的。所以,是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无度的欲望。这就决定着我们必须考虑掌握多大权力和掌握什么权力的问题,涉及到承担什么责任和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政党和政府远没有承担我们党和政府这样沉重的压力。按照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与洛克等人的政治理论建构起来的政治体制,概括起来讲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权力有限,按照权小责小、权大责大的原理,西方的民众对政党和政府没有过高的要求和期望。比如,人们经常讲在美国要见个州长、市长很容易,预约一下即可,门口也没有荷枪实弹的警察,而在中国不仅见省市领导难,就是见个县委书记也不容易。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改变了人民公仆的性质?显然不是,根本原因还是权力分配和权力运行决定的。在西方社会,如果精神出了问题进教堂,如果想赚钱进市场,如果发生法律纠纷就进法院,甚至许多公共事务也是由社会组织来完成。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下,党和政府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同时几乎承担了一切责任,所以就没有可能像西方那样处理官和民的关系,类似的问题不予以讲清,也便容易造成比较中对党和政府出现不认同。也就是说,一党执政,且有着无限承诺,永远执政,必无法卸责,那么就很难避免权大责大,期望高失望大。显然,这一点在革命状态下和执政状态下认识差异很大。革命状态时的政治斗争几乎一切围绕“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大大的”,这个过程甚至不太在意手段和方式。不仅这样,甚至权力集中的理念要表现到思想领域,也就是统一思维、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执政状态下利益和价值观出现多元,政党可以统一思想,社会却无法统一起思想来,充其量形成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观。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