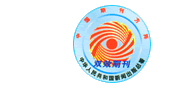郑永年:十九大,中国共产党重新界定自身现代性 |
||||
|
作者:郑永年 网站编辑:sxs3 来源:新华网 日期:2017-11-15
|
||||
|
|
||||
|
郑永年:十九大,中国共产党重新界定自身现代性(上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情。对中国本身来说,正如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一个总结过去、直面现实和通往未来的时代。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早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贸易大国,不管内部怎样发展,都会产生出巨大的外在影响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为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希望和动力。尽管十八大以后中国本身的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较之仍然没有走出危机阴影的西方经济,中国仍然是所有主权经济体中的佼佼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世界没有任何理由不关注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十九大。 十九大“自我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最为重要的信息便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现代性的重新界定。 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 十九大到底会如何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呢?这需要人们来解读十九大报告,因为这份报告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蓝图。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十九大报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外交等等,因为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高度综合的文件,多角度来解释不仅应当,而且必须。 不过,我认为十九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大会,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是政治,它是一个政治文件,虽然其它方面都有涵盖,但都居于次要和补充性的地位。在未来中国发展的很多问题中,政治是最关键的。其它方面发展规划会更详细地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我把十九大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进行的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通过这场“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重新界定了自己的现代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讨论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十九大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这里的讨论侧重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在强调“制度自信”的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关注正在发生的制度变化。为此,我们需要在十九大全方位的报告中,从丰富的内容中提取和勾勒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大构架。制度建设是十八大的主题,更是十九大的主题。 那么,就制度建设而言,十九大释放出什么重要的信息呢?简单地说,十九大“自我革命”所释放出来的最为重要的信息便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现代性的重新界定。经过“自我革命”,它演进成一个新的政党,或者说一个新时代的政党。中国所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都取决于政治的现代化。 当今世界面临的政治权力危机 要认识十九大所发生的“自我革命”,必须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政治权力危机,尤其是政党危机。不理解世界性的权力危机,就很难理解这场“自我革命”的世界意义。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政党及其权力都陷入了危机。从欧洲、美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核心危机”(或者“首脑危机”)的现象,无论给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核心危机”的核心便是政党危机。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可以被称为“现代的”国家,政党无一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政党组织社会、凝聚共识、产生领袖、治理国家。但在今天,所有这些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政治危机也随即产生。 在西方,今天的权力危机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当然,核心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核心,而是说西方所产生的核心没有能力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今天西方的政治核心或者统治集团至少表现为如下几类: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领袖集团,但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领袖很难说是最优秀的。从实际经验上看,这些被选举出来的领袖少有作为,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作为。这或许是因为领袖个人的能力不足,或许是因为领袖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结果是一样的: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领袖越来越多。最显著的行为就是领袖们经常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公民不可能通过直接民主行使权力,因此公民选举出他们的代表让这些代表来行使权力,这些代表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政治精英或者统治精英。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达成不了政治和政策共识,政治和政策之争最终演变成了党争,领袖在面临这种情况时不负责任地诉诸于公投,把事情交付给老百姓决定,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为直接民主。就其形式来说,公投的确是直接民主的最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本身对很多问题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对公投的结果又后悔,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一个社会的高度分化,社会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裂状态。可以说,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最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事务的动机。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化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因为无论是古希腊还是近代民主早期,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者有产者(主要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并且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替代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从前也发生过。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的时候,社会运动便会发生。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发动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为了反对殖民霸权,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民粹主义,也有右派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式的社会运动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领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各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者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转型,即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到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领袖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即往往不按现存规则办事情。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情,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是已经高度制度化了,甚至是过度制度化了,但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往往可以对现存政治制度造成轻易的破坏。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十九大会议期间,王岐山在参加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党的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仅在说、更是在做,无论哪个领域和哪方面工作,无一不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树立起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矫正“领导弱化、党建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情况下重新界定和获取现代性的。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是最重要的。没有这最后一个“全面”,其它三个“全面”就会无从谈起,因为前面三个“全面”都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行动主体去实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现代化”,其它方面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编辑:白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