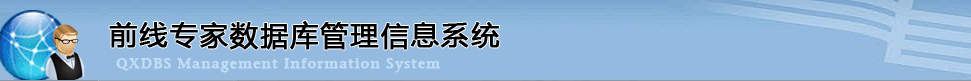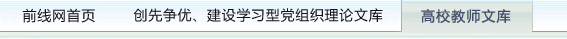|
| 东西互动中的“拿来”与“输出”
|
|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530 次
|
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中,“发现东方”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遭受到西方偏见是攻击可见一斑。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中有个很大的缺憾,那就是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包括五帝和夏、商、西周在内的2000多年未建立年代学标尺。从西汉的刘歆开始,历代学者就想尽各种办法推定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但2000多年过去了,始终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1]于是,在学界对《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疑古”中,人们只能从《三字经》模糊的记载中远看中国史前史:“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
1996年5月16日,国家“九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等四位首席科学家领头下,组织了多个单位的多位专家联合攻关,2000年底《夏商周年表》方案公布。《夏商周年表》的问世将我国的历史准确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2]但只隔了两天,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一篇题为《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怀疑》的报导,引述美国历史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批评说,这是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中国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3000年,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准上,表明这是一种政治和民族主义上的冲动。《远东经济评论》对此评论说:中国把夏朝列为中国神圣历史的证据,其意义等同于日本在1930年代吹嘘自己历史,中国发动此项工程的目的值得怀疑。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为题的一篇长文,摘译报道了这场讨论,然后《中国文物报》(6月)中花了一整版篇幅,予以摘要刊登。
在我看来,《纽约时报》、《远东经济评论》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是极不负责的说法,反映出西方学人中仍然存在相当强烈的文化种族偏见。虽然一些汉学家立场中肯,但有其他不少人附和西方媒介,不仅完全否定夏商周工程,攻击中国考古学的质量,甚至把对夏代历史性的正当学术性质疑,加码到对中国传统历史记载的无端怀疑,进而借古讽今,称中国学者对夏朝的“盲信”代表一种“文化灌输的危险意识形态”。不少西方学者继续怀疑夏代的存在,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问题很多,值得在分析批判的同时,认真地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3]
我意识到,“发现”和“输出”互相依存。至于“输出”首当其冲的是输出方式和途径问题。汉语言全球化在目前不具有可能性,因此,文化输出只有运用汉语-英语交互式方式阐释传播中国经典和当代文本,即用第一世界的形式(语言传播)传送第三世界的内容(思想文化)。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输出不可能是强制性的,而只能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当这种欣赏进入深层次时,进入文化的神经中枢时,西方就会打破语言的障碍,一窥东方文化的堂奥。正如李济所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辉才显得更加鲜明。把它关在一见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4]席泽宗也说:“历史上的东方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在起着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5]
在我看来,个体在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学术历程中始终应发扬两种精神:一是玄奘那种锲而不舍的“拿来”与融会的精神,二是鉴真和尚将中国文化和宗教全面“输出”的精神[6]。在这个意义上,发现东方是我们的心态,文化输出是我们的实践。要告诉西人一个真实的东方,不要让他们觉得中国人永远是愚蠢的。我认为当前重要的还是整理和输出,至于创造和转化等高级的文化输出还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
如果说,过去中国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饱尝恶果,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将重新确立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并且不再沉默、不再虚无、不再被文化殖民。中国文化学会了平等地看待事物的秩序和文化的演进,平心静气地看待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并愿意为这个强权世界转化为一个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而提供自己的文化编码。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经过现代性的反省,意识到我们在“发现”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立场和观念,使西方文化霸权在对话中很难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权力关系,从而达到改写世界的文明发展史,追问人类价值共性和本土差异性问题,构想未来世界文明精神生态意义的目的。世界不应该也不可能由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或早或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自己的声音在“自我言说”中逐渐进入“有效言说”[7]。在倾听和言说的“众声喧哗”中,人类将会找到自己的存在的多元地基。
正如赛义德所说:“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掺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8]我注意到,当今世界所有文化都不是隔绝的而是精神互动的,所有文化都不是纯粹单一的而是异质混杂的。没有所谓的不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文化,也没有不受东方文化影响的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彼此依存而休戚相关。正如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所说:“中国借助西方模式,能够使他为期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确立更加规范的准则,同样,我们借鉴中国的模式,可能会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权的礼的基础。它也许能提供更伟大的容忍精神,用以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并且能增强这样一种能力:它不仅使我们能看出自己的种种认识为西方所限,而且把这种限制当作人权观念的实际本质。”[9]应该反省那种冷战式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说法,关注核威胁下面的人类处境,使全球知识分子关注真正的问题——人性的良性发展和人类未来精神生态平衡问题。我意识到,人类文化史在不断造魅又不断祛魅中前进。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成为永远正确的思想,也没有任何文化体系可以永恒成为他人拿来抄袭的模式,没有任何话语权力的消长可以逃脱历史的意味深长的一笑。只有飘逝的才是永恒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重新发现、重新阐释、重新确立,一切都在互相交流中使可能性成为现实性。[10]
我坚持认为,新世纪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权力征服“东方”,而是如何重新“发现东方”。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起来。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本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不再自我陶醉也不再自我虚无,而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创新,进而坚定不移地走向文化“输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再次强调:“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决非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并促成新世纪世界文化生态达到新的平衡。
海明威警告过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孤岛,千万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那就是为我们自己而鸣。“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努力,或许就像西绪福斯神话那样,具有无法克服的悲剧和悖论色彩。然而我们毕竟在一种蒙昧混沌状态下清醒过来,我们毕竟看到了世界与我的存在之间的荒谬关系,寻找一种将“不可能性”变为“可能性”的方式:大石继续从山顶滚下,而西绪福斯也将继续将它推上山去。我很欣赏《易经》中的一句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谓富有;道并行而不悖,是谓日新”,这或许是我心中的理想境界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参李学勤著《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2页。
[2] 岳南著《千年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参《中原文物》“夏商周颠带工程笔谈”,2001年第2期,第21-44页。
[3] J.D.亨特:《文化战争》,安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转引自岳南:《千年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扉页题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 转引自岳南:《千年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扉页题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6] 鉴真和尚从743年起到754年止,历经11年,前后6次东渡日本,前5次均告失败。年届66岁高龄且又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仍然坚持东渡日本。可谓备受艰辛,屡遭磨难,终于达到东渡日本、输出文化、弘扬佛法的目的。
[7] 如果仅仅是自说自话,丧失了接受者的兴趣,这样的文化输出将是不彻底的。因此在我看来,强调“有效言说”已然成为文化互动中的重要原则。
[8] 爱德华•W•赛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3页。
[9] 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94页。
[10] 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