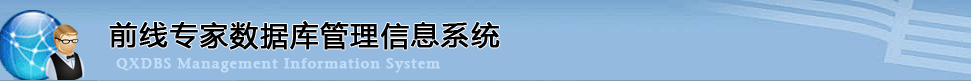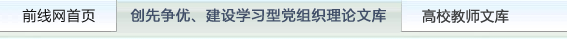|
目前有关社会管理“治理化”的许多定义和研究,只强调了社会管理是多主体参与的过程,忽视了社会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维护和发展好公民的社会权利,即个体在社会中享有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在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管理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实现和维护公民的社会权利;二是把多元化的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实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构化。但是,后者是以前者为前提的,前者的实现则以后者为条件。所谓的社会建设,就是社会权利的实践化与社会组织化、结构化的互动过程。
现代意义的社会权利
现代意义的社会权利,是由英国人马歇尔第一次系统论述的。他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中讨论了公民权这个概念及其历史发展路径。在他看来,公民权包括三个基本维度,即民事权(civil rights)、政治权(political rights)、社会权(social rights)。“民事因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各种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占有财产和签署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寻求正义的权利……与民事权最直接相关的机构是法院。政治的要素,我指的是作为政治权威机构的成员或此种机构成员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政府的参议会。至于社会的要素,我指的是从享受少量的经济和安全的福利到充分分享社会遗产并按照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与之最密切相关的机构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马歇尔认为,在英国,公民权的三个要素并非同时出现,而是经历了“浪潮式”的发展过程,民事权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对应于19世纪,到19世纪末期,随着公共基础教育的发展,社会权获得复兴并重新嵌入到公民权结构中。德国《魏玛宪法》颁布后,马歇尔据此将社会权利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最基本的经济福利与安全,二是完全享有社会遗产,三是普遍标准的市民生活与文明条件,四是年金保险,保障健康生活。
社会权利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使“社会权利”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宣言》的第22到27条谈到了社会权利的具体内容。《宣言》指出,“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第22条)1966年通过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则涉及到工作权、社会安全、免于饥饿、受教育以及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等。另外,1961年的《欧洲社会宪章》则承认人民享有工作权、公平待遇权、受教育权、健康权和接受社会救助等社会权利。
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报告》。报告所倡导的价值以及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大大推动了社会权利理念的普及,特别是其在各国政策制度中的实现。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类发展”理念是:人类尊严、全民人权、自由、平等、公平和社会正义是所有社会的基本价值,人类发展的目标是扩大人的选择能力和自由权利,并最终让所有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联合国设计的评价各国发展成就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三项具体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受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代表了人类的三种能力:健康长寿的能力,获得文化、技术和分享社会文明的能力,摆脱贫困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在联合国的倡导下,2000年,各国还签署了《千年发展公约》,确定了具体的新千年发展目标,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的八个目标中,有五个是社会发展目标。社会发展首先或绝对在提醒人们,发展的目的是人类和人类福祉,而不是物质或GDP数字。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世界峰会对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更加明确的概括:可持续发展包含“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三个组成部分”(有人将其称为三个支柱理论),会议认为这三个部分最好融为一体。但是,发展的目标既不是环境,也不是经济,而是社会,所以作为第三支柱的社会应当包括社会体制以及生活质量。
随着对公民权研究的深入,社会权利的内容也更加具体化。有学者将公民权划分为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社会权利包括:(1)促进能力的权利,如医疗卫生保健、养老金、康复治疗、家庭咨询服务;(2)机会权利,如学前教育、初等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教育咨询服务;(3)再分配和补偿的权利,如战伤抚恤、工伤抚恤、低收入者权利、失业补偿、侵权补偿。参与权利包括:(1)劳动力市场干预权利,比如劳动力市场信息获取权、就业安置、就业机会创造、免于就业歧视、就业保障;(2)建议、决定权利,比如劳资联席会、协调会、集体谈判权、共同决策权(人力资源决策);(3)资本监控权利,如工薪者基金、中央银行调控、地方投资决策、反托拉斯和资本逃逸法、共同决策权(战略决策)。显然,从广义上说,这里谈到的参与权利也属于社会权利的范畴。
社会权利的实现
对社会权利的考察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权利的一般发展过程以及社会管理富有启发意义。
第一,社会权利是作为社会成员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资格和拥有文明生活条件的权利。但个体享受的社会权利,不同于个体的自由,是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实现的权利。因此社会权利在本质上不是占有,而是分享;不是是否拥有,而是是否实现;不仅仅是获得社会利益,还是对整个社会的责任。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存续,就必须使社会的每个组成成员都享有基本的共同权利,这样才能使社会成员之间有相互交往与合作的基本制度条件,也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形成基本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内部的分化越剧烈,就越需要这些基本的共同权利,以缓和可能出现的冲突与矛盾。
第二,社会权利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的。马歇尔谈到的公共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需要,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经济发展水平下才能够得到实现,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可以享受到的普遍权利。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提出,是对市场力量的抗衡。这一点在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那里得到了充分论述。他对三种福利资本主义的分析就是从社会权利出发的,三种不同的模式表明了社会权利实现和保障的三种不同制度结构。在他看来,社会权利是“‘非商品化’的容纳能力”。判断社会权利的标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人们依靠纯粹市场力量之外的力量去改善其生活水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权利削弱了公民作为“商品”的地位。
第三,社会权利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福利国家制度就是围绕社会权利的实现而形成的一套制度。尽管对于福利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看法是,福利国家就是对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富有保障责任的国家。国家不仅赋予社会成员一定的权利,还要处理与市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而正是在处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社会权利不再只是个人的权利,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权利,即社会权利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的一种“生产性投资”。
第四,与公民权的其他组成要素相比,社会权利的实现过程更为复杂。之所以如此,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社会权利的实现是通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来体现的,所以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二是社会权利的实现涉及社会各阶层关系的调整以及国家、家庭、企业、社会各类组织的功能调整,是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重新分配的过程。
这些研究说明了:社会权利内容的界定以及权利的实现途径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制度条件决定的,每个国家都应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权利实现制度。这点得到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肯定。正如米什拉所说,“一个国家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在任何既定的时刻,国家也有一套制度来规范生产和分配,管理冲突,制定社会决策和维护社会价值观。”
社会权利的实现是普及资格和增强能力的双重过程
普及资格就是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就,增强能力则体现为社会权利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个人和社会组织组织能力的提高。没有社会主体性的建设,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权利实现。因此,均权和赋权是社会权利实现过程中一个硬币的两面。赋权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有助于用“社会本位”的新的发展范式来替代长期形成的“经济主义”的发展范式。后者把社会权利的实现简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提供,忽视了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才是社会权利的核心。
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时候,早就说过“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只有这样,也必须这样,才能够使得“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从能力角度对发展理论的研究,深化了当代对社会权利包含的“赋权”内容的认识。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是与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而能力的提高有赖于自由的实现。发展应该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拥有更多的自由。而个人的可行能力严重依赖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安排。经济条件、政治自由、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以及防护性保障这些工具性权利与自由的实现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生活得丰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