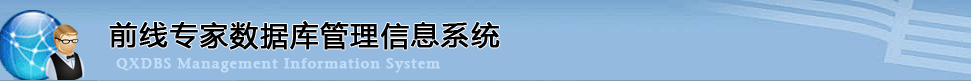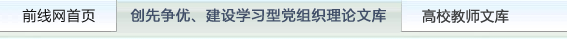|
| 县域政权改革的逻辑
|
| 作者:杨雪冬 日期:2013-04-28 阅读:4831 次
|
|
已经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县制是世界上最悠久,也是一直沿用至今的地方政府体制。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相较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差别,也是支持中国政治统一的基础性制度。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的“政不下县”,还是近代强调地方自治的新县制改革,抑或是当代县域管理的党政结构,县这个政权层级都拥有完整的国家管理和控制功能以及相应的组织安排、工具手段。相对于中央来说,县是最完整的微观国家;而相对于社会来说,县又是离其最近的现实国家。
目前的县级政权运行由党政结构决定的。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县制传统,但是现行的县域管理体制是由共产党重新构建起来的。建立的基本方式是先建党,再建政,然后由政党动员和构建社会,形成对政权的合法支持。虽然在县级建立了完整的国家权力机构,实现了明确的制度分工,但是无论从纵向关系,还是水平关系上,党委都是推动这些组织机构运行的体制动力,政党管理方式的变化直接决定了政权运行方式的变化。在高度垂直化管理的政党体制下,县级党政结构单一化为党的地方组织。
改革开放给县级政权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县级政权开始恢复微观国家的地位。一方面,下放权力成了国家和党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县级政权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尤其是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在党政分开原则指导下,县级政权机构的分工更清楚,运行的独立性也有所扩大。“五大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律监察委员会)成了县级政权的基本架构。尽管各级政权结构类似,但是县级政权以书记为“一把手”的运行机制更具有个人化色彩。人大、政协由于没有人员进入常委会,所承担的法定职能失去了现实权力的支持,造成了县级政权内部结构失衡,运行高度党委化,并强化了“一把手”权力。而县域内公共舆论和公民社会的不发达,进一步彰显出这种个人权力扩大的潜在危害。
因此,在县域政治中,形成了一种悖论性的现象:一方面县级政权抱怨上级权力下放不足,干预过多;另一方面县级政权的领导者在县域范围内又有着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即便存在着不断加强的垂直控制。县级政权——这个微型国家拥有了畸形化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发展经济方面得到充分发挥,并适合了经济效率的要求。县级党委通过中心工作机制将所有的国家政权机构都动员起来,后者无论是职能运转还是资源投入都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在社会对财富增加渴求的背景下,官方的经济增长逻辑普遍化为社会的要求,并从国家道德层面消除了一些社会群体对具体经济增长政策措施带来的消极后果的抵抗。由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了党的意志、国家目标和社会共识,所以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县级政权无论在体制内还是社会中都获得足够大的空间。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中,公共权力空间的扩大为权力的“私有化”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所有物品和关系转化为商品提供了可能和理由,另一方面,交易的逻辑也跨越了还没有定型的公私边界,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具有畸形自主性的县级政权面临着急遽腐败的侵蚀。与资本勾结和与黑恶社会势力沆瀣成为两种典型形式。一些县级政权严重脱离了体制控制,丧失了对县域社会安全和公正性维护的基本功能。无论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县级政权公共性蜕化的现象。
以避免地方利益坐强为基本目标的“异地任职”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蜕化。一方面,到异地任职虽然会与地方势力保持距离,但是也不容易对任职区域形成认同。县域社会固然规模更大、关系更为复杂,但依然是“熟人社会”。地域认同对官员形成构成了情感约束和道德制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县级党政首长调动频繁,“空降部队”增多(多从上级直接调任,几乎没有本地干部提升的可能),更抵消着这种地域认同的形成,也放任了政治投机心理。“流官”替代了“父母官”。一些个人毫无顾忌地实现着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本地干部的心理也有失衡的倾向。在经济上,大部分县的干部收入明显低于地级市、省会城市的同事,在政治提拔了,有限的县处级职位也使许多人无法企及;在岗位上,又不断受到干部年轻化和用人“个人化”的冲击。本来依靠家乡情感保持高度稳定的县域干部群体反而成了最不稳定的群体,责任意识受到严重削弱。大批有着丰富经验的官员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进入了经济领域,使县域经济进一步官僚化,并推动了县域政治生态的恶化。
当然,以干部体制为核心的垂直控制在方式上也在增多。县级政权内部也在形成某种非正式的“一把手”制约机制。一是党政一把手矛盾的加深和显性化,县委书记的“拍板权”受到了县长的掣肘。但是县长通常又是县委书记位置的第一接替者,这为县级决策更改频繁埋下了隐患;二是县委常委成员数量的增多,公安局长、实力派副县长、县委政府两办主任等在许多地方都进入了常委班子。人大、政协作为民意机关继续被排除在县级政治决策之外,而公安局长政治地位的提高,又破坏着党委领导下的司法体制内部关系的平衡,法院、检察院的地位相应被削弱。因此,这种非正式制约机制,虽然存在着分散“一把手”权力的可能,但更可能造成县级政治向“实力化”蜕变,体制内部关系更加不平衡。更危险的是,这种“实力化”也容易简化为“金钱化”,职位直接代表着经济实力。
县级政权运行的绩效日益与“一把手”的能力、素质、自我约束程度等个人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些所谓的“政治强人”或“铁腕书记”频频出现于各地的政治版图上。客观地讲,这些个人的大部分行为对于县域政治生态的改善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因为他们执政的方法多是高压驱动型,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虽然有效发挥了地方自主性,但也充分暴露了个人权力过大的弊端。形象工程、决策个人偏好往往是这些政治强人留下的遗产。
随着各类资本投资的扩张,掌握较齐全的生产要素(最突出的是土地、自然资源)的县在经济重要性上也在提高,县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县级政权希望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自主权。这种要求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积极回应,以打破现有城市化方式对农村造成的资源汲取,形成资源的反向流动,恢复农村与城市的平衡。这是“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必然会产生提高政治地位的要求。县域治理恶化增加了这种要求的筹码,因为县域内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能控制在特定范围内,必然会对上级政权乃至整个体制产生冲击。“一把手”的重要性再次体现出来。必须在制度上为这些管理着微型国家的“一把手”建立起有效的政治激励。因此,我们看到了今年以来中央要求县委书记任命权上收到省委,各省提高部分县委书记的政治级别等举措。这对于一直抱怨县里工作条件艰苦,晋升渠道有限的县委书记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也会缓和党政一把手之间的摩擦。但是,从长期看来,如果缺乏其他配套机制,这些措施很可能会进一步助长县域政权自主性的扭曲,因为书记权力的强化会加剧县级政权内部结构的失衡。
总结过去30年县域政权的运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放权和政治整合(或控制)一直是推动其变化的两个主要动力。由于县域政权内部结构的失衡以及县域社会发育不够,使得这个微型国家的自主性呈现出畸形状态,即自主权的扩大集中体现为个人权力的弱约束化。面对日益增强的社会要求(数量上和渠道上),拥有这种畸形自主性的县域政权显然疲于应对,甚至会由于个人权力的过大引发体制内部的抵制和社会的不服从。因此,单纯地依靠政党体制的政治整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权力弱约束问题。这就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恢复县域政权内部结构的平衡和推动县域社会的发展。前者需要回到现有的宪法框架下,恢复和强化县域政权各组成部分法定的功能;后者则需要为县域内公民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一个法治与民主同步进行的过程。这也是重新思考“郡县治天下安”这句话含义的现实背景。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杂志2009年11期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