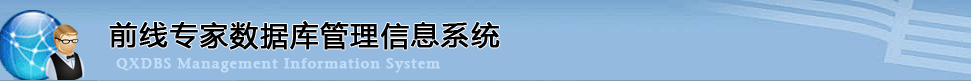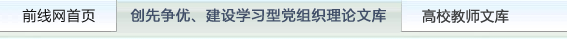|
| 论公共管理者的仁爱品性
|
| 作者:张康之 日期:2013-03-15 阅读:1123 次
|
|
[摘 要] 在对社会治理活动的伦理审视中,我们发现,如果在人类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者的仁爱道德品性缺乏客观保障的话,那么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则要求治理者必须把仁爱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来加以承当。公共管理者的仁爱是博爱与自爱的统一,他能够承当这一道德责任和义务是他成为合格的公共管理者所应具有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公共管理者;仁爱;博爱;责任和义务
在农业社会,社会治理者主要是国家官吏;在工业社会,社会治理者以政府中的行政人员为主要构成部分;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者则被称作为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者是一个独特的职业群体,是专门从事社会治理工作的职业活动者。由于公共管理者是在公共领域中为了公共利益开展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所以,他除了需要从事这一职业活动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之外,还需要得到他个人的道德品性的支持。其实,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伦理关系都是一种公共关系,一切伦理都是公共的,对于孤立的个人来说,不需要“伦”也没有“理”,在财产的问题上,有“公”“私”之分,但在伦理问题上,没有什么“私人伦理”或“公共伦理”的区别,如果有人造出了“公共伦理”的概念,那是极其可笑的一件事情。公共管理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管理活动,所以它会集中体现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具有公共属性的因素,伦理关系、伦理原则以及道德规范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然会要求公共管理对它有着更多的体现。可见,公共管理的性质决定了公共管理者应当拥有开展公共管理活动必备的道德品性。
一、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仁爱
在公共管理者的诸多道德品性中,仁爱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品性。在一般伦理学中,仁爱是人与他人相与为友的德性。但是,从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比较中可以看到,在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与被治理者之间是统治的或管理的关系,没有也不允许有相与为友的要求。所以,仁爱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治理者的德性。公共管理不同,它是后工业社会中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平等与合作所要求的恰恰是人们之间的相与为友。因而,仁爱也就成了公共管理者必须承当的责任和义务。
仁爱往往被人们感觉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和赠与,是权力关系的道德体现。在历史上,确实是这样。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仁爱是贴敷在权力之上的道德外衣。因为,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鲜有来自外部的客观力量对它进行日常性的制约,人们只有期望掌握这些权力的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仁爱,越是对于那些在权力体系中处于高位的人,人们对来自他们那里的仁爱的期望越强烈。对于处于权力关系最底层的人们,是没有仁爱的要求的。所以,仁爱总是表现为君对民、主对仆、上司对属僚、父对子的恩惠和赠与,是在单一权力关系基础上生成的纯粹主观性的道德责任和义务。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当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取代了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之后,权力与道德的姻亲关系开始解体,权力与法律之间建立起了若即若离的矛盾统一关系。虽然,权力依然处于整个治理体系的轴心地位,但权力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法律的日常性限制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道德外衣被剥夺殆尽,成了赤裸裸的强制性力量。因而,人们再也不能够从权力执掌者那里看到仁爱的踪影。权力越是受法律限制和约束,权力执掌者就越没有仁爱的道德表现。
不过,仁爱的存在基于两个必要前提:第一,需要存在着权力关系;第二,执掌权力的人只有道德化的可能性。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存在着权力关系,但执掌权力的人却不具有道德化的制度和文化基础。我们知道,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单一的权力关系作用体系,同时也要求权力执掌者道德化,而且这种要求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期望。但是,作为统治者的权力执掌者能否道德化,是缺乏客观的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来提供保障的,社会除了周期性的王朝更替之外,没有一个日常性地淘汰不道德权力执掌者的机制。因而,权力执掌者的仁爱不被作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而是被作为一种统治者的美德。在公共管理中,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一体化,有效地解决了上述所有问题,特别是使权力执掌者的道德化有着客观的保障机制。
在公共管理中,仁爱不是作为权力执掌者的美德,而是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公共管理者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不管他在公共权力的授权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也不管他执掌的权力大小,只要他一俟与权力联系在一起,他就同时拥有了仁爱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他所拥有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在与其他所有公共管理者所应有的仁爱的比较中,是没有质和量的区别的。最为重要的是,仁爱在公共管理中不是美德,而是责任和义务。因为,一切与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美德都必然表现为恩赐和赠与,但作为责任和义务,则是一种客观要求,是必要的承当。虽然仁爱作为道德责任和义务,来源于公共管理者的自觉,是他自觉了的责任和义务,但当这种责任和义务发生在公共管理活动之中的时候,则是一种必要的承当,而不是取决于公共管理者的主观意愿,他必须承当这种责任和义务,如果他逃避承当这种责任和义务,他就会失去了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资格。
可见,虽然道德责任和义务是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自觉,但却是一种必然的自觉,而不是作为他个人的纯粹的自主选择。一个普通的人,在道德自觉的问题上,可以在“能”与“否”之间进行自主的选择,但作为公共管理者则不具有这种自主性。美德与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即使对于公共管理者,也是有着充分的自主性的,一个缺乏某项或某些美德的人,依然可以担负公共管理职责,但是逃避了责任和义务的公共管理者,就失去了作为公共管理者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之,我们倾向于把仁爱规定为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看作为公共管理者的美德。
二、仁爱是博爱与自爱的统一
仁爱是人的道德存在的形态,这种爱与那些基于情感的爱不同。基于情感的爱是非常具体地指向特定对象的爱,情感之爱与其说是奉献,到不如说是占有,是由于人的占有欲而生成的爱,而爱本身又反过来增强着人的占有欲望,即使这种占有在物理意义上不能成为现实,也能够在心理上得到实现,或者,情感之爱会以情感宣泄的方式而得到实现。这种基于情感的爱,往往在男女之间会有典型的表现。在人的爱中,随着情感因素的淡泊,爱的对象的明晰性也会淡薄。比如,在人对弱者的同情中,对残障者的怜悯中,情感因素与特定的男女相爱相比要弱的多,而道德因素却要多得多。同样,在父子母女之爱中,虽然是以情感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在这种爱的深层更多的是道德因素,是人类历史积淀下来的道德因素在发挥作用。
根据功利主义特别是利己主义的理解,父子母女之爱属于人的自爱,即人把子女看作为自我的延续、延伸和证明。这种解释似乎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在人类之爱与动物之爱之间建立起了统一的解释框架,使牛的舐犊与父母对子女的抚摸有着共同的可理解性。但是,我们认为,人的爱毕竟是与动物的爱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动物是否有爱,或者说动物的行为中是否包含着爱,主要取决于人的理解,人若从动物的行为中解读出了爱,那就有了爱,人若没有从中解读出爱,就很难说动物的行为有爱,即使有,也是属于低级情感类型的爱,而不具有道德性。在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中,我们发现不同的人对子女的爱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别,那些“动物性”特征较强的人,对子女的爱较为有限,他可能为了某项暂时的利益要求而溺婴;相反,那些“人性”较强的人,对子女的爱也就较深,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为了子女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
可以这样认为,情感之爱与人的物理欲求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人的物欲支持这种爱,也为这种爱的生成提供动力,纯粹的情感之爱往往表现为实现物欲的要求和冲动,最为经常地是表现为与性欲之间的密切联系。道德之爱与人的物理欲求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道德之爱是平静的、纯洁的,可以不以任何自我满足的欲求出现。属于人的爱是道德的,道德的爱是恒久的,如果在这种爱中也加入情感的爱,那么这种爱就会显得更为强烈。情感的爱是短暂的、暴发性的,如果没有道德之爱的支持,也是脆弱的。当然,人是有道德的,所以人的情感之爱并不总是表现地向流星那样一闪即逝。但是,在一些社会道德水平较低的历史时期中,人的情感之爱的易逝性、暴发性特征也会表现的比较明显。因为,在这些时期中,人的情感之爱往往会表现出泛滥的情况,而道德之爱则受到了冲击,或者被深深地掩盖在情感之爱的背后。道德的爱是仁爱的基础,或者说,道德的爱能够生成仁爱。当道德之爱以仁爱的形式出现,它就不是针对于具体的对象的爱,而是启蒙学者所称的那种“博爱”。如果说人们在这种爱的表现中发现了它指向具体的特定的对象的话,那么其背后必然有着情感因素。道德之爱是敦厚宽容的,不像情感之爱那样易于产生嫉妒和易为转化成怨恨。对于社会治理者来说所应拥有的正是道德之爱,如果说以往社会治理模式的性质无法为其治理者拥有道德之爱提供可靠的保障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则会把造就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之爱作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基本目标,公共管理者的这种道德之爱也就是仁爱。
但是,仁爱又可以看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爱,虽然它不是功利主义所讲的那种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造成的自爱,却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自爱,是在博爱中实现了的自爱。以占有为实质的情感之爱是狭隘的自爱,相反,道德之爱虽然也是自爱,但却是以自爱为基础的博爱,是通过博爱而得以实现的自爱。所以,道德之爱中的自爱决不意味着自私,反而恰恰是自私的否定。年轻人常讲的“爱是自私的”,那是仅仅就情感之感而言的,道德之爱则恰恰相反。在个人的私人生活中,情感之爱是作为一种自私的爱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在公共领域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人,它的爱却应当是道德之爱,他只有有着博爱的品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自爱,否则他就是不自爱的。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博爱与自爱是统一的,是在道德基础上的统一。
一个人的自爱首先体现在热爱生活上,对生活的热爱又会不断地升华到对生命的热爱。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必然会引导着人也去主动积极地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和体验生活,进而去发现生命的意义。这个时候,关于生活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就不会仅仅被用来对待他个人,而是会推广到对他人生活和生命意义的承认。冷冰冰的铁的无私往往导致人在人格上的自贱自戕,因为他完全不理解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他无以自爱也就不会爱人。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无论他所掌握的权力大小),都会以危险的“暴君”的面目出现,他会蔑视他人的生活、压抑他人的欲求,甚至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不仅那些纵情于声色的君主荒淫无道,而且那些近乎于禁欲的君主往往更为残暴,会完全无视他人生命的价值。所以说,仁爱作为一种博爱又是来源于自爱的,而自爱又起始于对生活乐趣的体尝,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这就要求公共管理者为了承当仁爱这一责任和义务,就要从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美学修养起步。
三、作为责任和义务的仁爱
仁爱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源于他自爱的德性。莱布尼茨在德性的意义上把仁爱规定为一种“普遍的慈善”,他说:“仁爱是普遍的慈善,而慈善是爱或尊敬的习惯。但是,去爱或去尊敬是从别人的幸福中取得快乐,或者,换言之,是把别人的幸福当作我们自己的。这样就解决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怎样才能有一个无私的爱。”[1]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仁爱就不仅是一种德性,而是他的职业本性所决定的责任和义务,他能否承当这一责任和义务,也是他是否自爱的标志。在一般的意义上说,一个拥有仁爱品性的人,也必然是自爱的。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要求把仁爱确立为公共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并不是满足于要求公共管理者在行为上表现出仁爱,而是要求他承当这种责任和义务时出于他的本性冲动。这样一来,仁爱就不再是他刻意追求的外在行为表现,而是以他个人的自爱为基础的,他承当了仁爱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意味着他是充分自爱的,所以,作为责任和义务的仁爱,是公共管理者的博爱与自爱的统一。
如上所说,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仁爱、公正、求实、宽容等等,往往被看作是社会治理者的美德。其实,作为美德只是一个治理者可有可无的东西。有了这些美德,使治理者成为高尚的人,成为人们敬仰和赞颂的“清官”:没有这些美德,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治理者而存在。但是,这些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模式中被当作美德的东西,在公共管理中则被作为责任和义务的内容,一个人在选择了公共管理职业的时候,他同时也必须选择这些责任和义务;一个人在被选择为公共管理者的时候,他也同时被赋予了这些责任和义务,他如果不能选择和接受这些责任和义务,也就会被弃除在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之外。
我们提出公共管理者的仁爱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是美德,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仁爱作为社会治理者的美德而存在时,它可能会对这些社会治理者行使权力的方式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些社会治理者本人却并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当仁爱作为为责任和义务而存在的时候,就不再给予治理者们以恩赐和赠与时的快乐,而是给予他们以道德约束和限制。仁爱反映的是权力关系,是与权力的存在相关联的,当仁爱还是权力执掌者的美德的时候,是权力之树上开出的奇异花朵:当仁爱成为权力执掌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它已不再是花朵,而是丰硕的果实。虽然在公共管理中,仁爱依然是与权力相关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但仁爱却不是对权威的展现,也不是依靠权威和为了证明权威的行动,更不是证明权威的手段。一切依靠权威和为了证明权威的行为,都超出了可以进行道德判断的范畴,因而,试图把仁爱作为证明权威的手段的做法也必然是非道德的。在公共管理中,仁爱作为道德责任和义务,是公共管理者的必要承当,“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可以看作对公共管理者承当这种责任和义务的最好的描述。
参考文献:
[1]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此文发表于《甘肃理论学刊 》2004年第1期 )
|
|
|
|
|